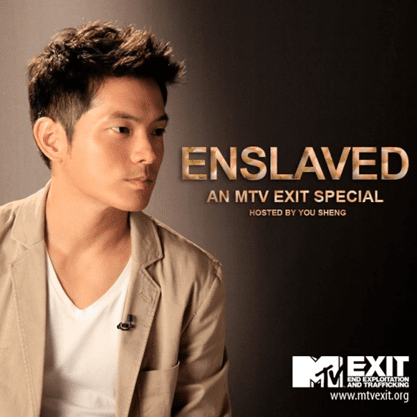評論:保護還是壓迫?-再思「反人口販運」
在台灣,「反人口販運」(anti-trafficking)一詞在 NGO 圈或對關心社會議題的朋友而言,應該並不陌生。根據2009年公布的〈人口販運防制法〉,「人口販運」的定義,除了指透過不法方式迫使人從事性交易外,亦包括:勞動與報酬顯不相當、器官摘除等不同形式的剝削。
「反人口販運」的在地歷史可追溯自198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對少女(其中許多為原住民少女)遭原生家庭販賣,被迫從事性行為之現象產生關注。因應此議題,「婦女救援基金會」、「展翅協會」(原「終止童妓協會」)等團體接續成立;1988年,婦女團體與原住民團體並展開「1988年救援雛妓大遊行」。
2000年之後,由於聯合國、美國、歐盟對「人口販運」議題以及國境控管的關注,連帶影響台灣對此議題的重視,政府挹注許多資源進行「人口販運防制」。民間團體(例如,以「反人口販運」為創會宗旨的「婦女救援基金會」、「展翅協會」,以及之後加入此陣營的「勵馨基金會」)也組成「反人口販運聯盟」,呼籲對此議題的重視。除了組成聯盟,監督政府在人口販運防制工作上的努力,這些團體同時也接受政府委託,以公辦民營、或行動方案等方式,成為政府在民間的「夥伴」,協助人口販運被害人安置庇護。
乍看之下,「反人口販運」並無什麼不妥,任何形式的剝削-性剝削、勞動剝削、身體剝削,本就應該被看見、譴責、防制。然而「反人口販運」的興起有其特定脈絡,過去也已有論者為文檢視台灣的「反人口販運」,在美國主導、由上而下的全面發動下,除了迴避了外籍勞工勞動剝削的處境,亦淪為政府控管國界的障眼法,與混淆民間視聽的假議題。
身為社會工作者,我曾與台灣政府對跨國婚姻的嚴格管控正面交手,在「假結婚、真賣淫」這類台灣社會對東南亞新移民的特定印象下,政府對東南亞跨國婚姻之管控從國境之外就已開始。婚姻移民必須通過官方辦理的「結婚面談」,才能順利來台與配偶團聚。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在團體與政府單位的協商過程中,當團體質疑政府透過面談、訪視等手段,管控婚姻移民入境與居留的權利,恐有「戕害家庭團聚權」之虞時,政府單位的回應卻似有意無意的有種「驕傲感」──似乎讓越少移民進來,越能證明他們確實「抓到」了「假結婚」的嫌疑犯,因此捍衛台灣國土安全有功。這樣的思維,現在回想起來,大抵和「反人口販運」脫不了關係。
如果「反人口販運」是兩面刃,其在幫助了人口販運被害人的同時,也賦予了國家更多權力,對人民進行管控。那麼,究竟「反人口販運」產生了哪些問題?
----------
接下來,本文將翻譯Briarpatch Magazine於2010年時收錄的一篇很有趣的訪談對話錄,訪談的對象為Nandita Sharma與Jessica Yee。Nandita Sharma為社會運動者、學者、以及《反人口販運的修辭以及構建種族隔離》(Anti-Trafficking Rhetoric and the Making of a Global Apartheid)一書的作者;Jessica Yee則是「原住民青年性健康網絡」(Native Youth Sexual Health Network)的負責人。這篇文章雖是舊聞,但現在看起來仍充滿真知灼見,期待透過引介與摘譯,能帶給關心這個議題的朋友多一點不同的想法與刺激。

「我們不應該賦予國家更多權力去懲罰勞工,反倒應該給勞工更多力量去對抗剝削。」-Nandita Sharma。
(圖片來源)
問:政府與媒體如何使用「性奴隸」一詞創造道德恐慌(moral panic)?對移民女性從事性工作的影響為何?
Nandita Sharma:大多「反人口販運」的支持者,都希望能降低女性進入性工作的可能性,並主張以懲罰性工作,作為防止移民女性進入性產業的手段。例如,在加拿大,國家對移民女性從性工作的監控越來越嚴苛。警察在維護「公序良俗」、「公共健康」的旗幟下,增加對脫衣酒吧、按摩店的查緝;同時,也有越來越多的移民警察(immigration police)尋索所謂的「人口販運被害人」。
當然,大多數的移民女性並不從事性工作。但對那些從事性工作的女性而言,她們面對最大的威脅之一,就是她們的公民地位。缺乏永久居留的權利,使得從事性工作的移民女性十分脆弱。這些移民女性或依靠短期工作簽證居留加國,或被迫非法工作。而雖然加國人民對性產業的需求很高,但移民卻不可能透過從事性工作取得合法居留加拿大的入場券。「反人口販運」運動打擊這些女性的工作能力與機會,同時,也進一步正當化「女姓不應該涉入性產業」的想法。最後,這些被創造出來的道德恐慌,使得從事性工作的移民女性的處境更加艱困。
問:「反人口販運」如何與促進「女性權利」與「女性能動性」這些目標絕緣?
Nandita Sharma:由於政治與經濟的危機,移民的數目也越來越多。過去十年,世界各地的政府陸續通過「反人口販運」相關法律,「第一世界」(First World)國家更爭先通過限制移民合法進入國家的政策法令,使得許多跨國移動的人被認定為「非法」。
反人口販運立法常被用來對付「非法移民」。「反人口販運」往往不譴責那些限縮移民權利、迫使她們處於「非法」狀態的法令政策,而是針對那些跨越邊境的人民。由於在現代世界中,若缺乏協助、或官方認可的文件(例如簽證、護照),跨越國界的移動幾乎不可能達成,因此「反人口販運」也懲罰那些媒介移民跨越邊境的人,透過這些方式,反人口販運合法地強化國家對邊境的管控。
問:若不將女性為人口販運被害人,我們如何對抗性產業對女性的剝削?
Nandita Sharma:要回答這個問題,可從性工作者本身得到線索。性工作者組織一直致力於促進性工作更加安全、有尊嚴、報酬合理,她們的首要任務是除罪化(decriminalization)。然而「反人口販運」卻往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反人口販運」加重了對性工作的查緝與懲罰,尤其是針對性工作媒介者。事實上,終結性工作、與提倡性產業工作條件這兩個理念之間,存在著根本上的歧異,其癥結點在於-女性究竟有無權利從事性工作。「反人口販運」陣營認為女性只要從事性工作,必然會受到剝削。但是我和多數性工作者的組織,並不認同這種說法。如果人們停止對性工作者的歧視,性工作是可能更安全與有尊嚴的。除了對抗歧視之外,我們同時也應該支持性工作者組成工會組織─這正是在印度、孟加拉、舊金山、許多地方的性工作者組織正在努力嘗試的。對女性而言,性工作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一個可能的選擇。我們需要理解,人們需要工作,而性工作,對許多女性而言,即是一個可能的選項。
再者,如果我們希望終結對女性的剝削,我們必定要挑戰資本主義,因為它是所有剝削形式的根源。無論我們是在性產業、餐廳、大學工作,我們都可能面臨被資本家、或其他因剝削勞工而獲利的人剝削的處境。因此,如果我們希望終結剝削,我們不應該賦予國家更多權力去懲罰勞工,反倒應該給勞工更多力量去對抗剝削。長期以來,女性主義者致力於倡導女性應得到自由,而自由,包括掌控身體、與情慾的自由。因此,女性主義者的抗爭,不該排除對從事性工作女性的支持。
對「反人口販運」持批判態度的人士常被扣上「不關心女性」的帽子,他們被控訴為不關心那些被綁架、被毆打、被俘虜、被剝奪報酬、或是護照、身分證件被奪去,以致自由受控制的女性。然而,我們應該認知到的是,這些犯罪行為早已規範於加拿大的〈刑法〉(Criminal Code)之中。綁架、毆打、強暴、剝奪報酬、強制扣留證件都是非法的。如果在既有法律的規範下,警察對取締這些犯罪行為與保障女性安全,似乎沒有太大興趣,那麼,為什們人們會認為,新制訂「反人口販運法」就能保障女性的安全呢?相較於「反人口販運」法制化,我們更當要求的,是保障性工作者和其他勞工一樣,能有基本的健康與安全保障;以及無證勞工(illegalized worker)也應擁有與一般勞工一樣的權益,以消弭對無證勞工的制度性歧視。懲罰媒介女性移民進入國界的人,絕不是保護女性的唯一管道。
問:如果限制性移民政策,反倒造成「被販運女性」受剝削,我們當如何保障移民女性的安全?
Nandita Sharma:讓移民女性更加安全的唯一之道在於「去刑罰化」(decriminalize)。我們應肯認人民有自由移動的權利。如果當代女性能自由移動-不需承受刑罰;不需偽造文件;不需藏匿在船艙或運用其他更危險的交通方式-她們的人身安全會更受保障。
反之,「反人口販運」立法以取締無照移民仲介作為政策目標,增加移民跨越邊界的成本,結果是使得移民必須借款、欠債,才能完成移動的夢想。況且,由於對仲介的刑罰越發嚴苛(在加拿大,相關刑責最重可判終身監禁;在美國,可能被判到死刑),使得他們引介移民跨越國界的路線越來越危險,以規避查緝-跨越沙漠、翻山越嶺成為家常便飯,許多移民在這樣的過程中失去生命。由此可看出,「反人口販運」立法,雖名為保障女性,但實是使移民女性面臨更大的安全威脅。
問:請妳談談加拿大原住民女性面對的強迫勞動與剝削處境。而對原住民的特定歷史脈絡而言,妳對「販運」(trafficking)這個詞彙的看法為何?(圖片來源)
Jessica Yee:在加拿大,原住民女性遭受強制勞動與剝削處境,已有長達500年的歷史。有趣的是,媒體似乎是到現在才對這個議題有興趣,突然之間,大眾開始關心起被謀殺與失蹤的原住民女性,也開始意識到,18歲以下的原住民女性受到性騷擾的嚴重性。雖然媒體直到現在才開始關注這些議題,但如果你問任何一個原住民,他會告訴你,女性被強行帶離原住民社群、政治與權力地位被弱化,根本不是件新鮮事。
我認為「販運」這個詞彙難以真實表達加拿大原住民女性所面臨的處境。身為原住民女性,我經歷許多壓迫與暴力。在街上,在辦公室,我都可能遇到性騷擾與惡意對待,而我的經驗告訴我,國家或是警察對我的幫助往往是薄弱的。由於原住民女性被認定為較劣等,因此對原住民女性的暴力常被「正常化」,也成為原住民女性普遍內化的認知。
人們討論到「人口販運」時,性工作、與牽涉國界跨越的人口販運常是被關注的焦點。但我們必須提醒自己的是,性奴隸與強迫性行為不是剝削的唯一形式,我們也應關注國境內部、針對原住民的販運。
許多人混淆「販運」與「性工作」這兩個不同的概念,他們認為性剝削是強迫勞動的各種形式中最嚴重的議題。但事實並非如此。國家將全副精力投入在查緝色情按摩店、以及取締性工作者的結果是,那些被販運、被強迫跨越邊境的人得到更少的關注。這些行動美其名為「拯救」女性脫離火坑,但實際上卻是更進一步「殖民」女性的身體、空間、以及剝奪她們的自主選擇。
問:你可以談談「反人口販運」運動如何影響從事性工作的原住民女性嗎?對於政府試圖將「反人口販運」,操作成對女性權利的支持,妳有什麼看法?
Jessica Yee:最近,加拿大薩克屯(Saskatoon)的保守派議員Brad Trost試圖提案、取消政府對「加拿大性健康聯盟」(Canadian Federation for Sexual Health)與「國際生育計畫基金」(International Planned Parenthood Fund)的補助,因為這兩個組織支持性工作與墮胎權。為了合理化他的提案,他辯稱他真的很關心女性,並且關注女性如何被暴力相待、被強迫以性工作做為職業,因此才衍生墮胎的需求。我認為這件事很重要,因為由此可看出,政府與媒體,不過是運用貌似左翼與捍衛人權的說詞,來推動右翼保守的政策。
將販運等同於性工作的誤解,反映的是對性工作本質的無知。多數「反人口販運」陣營並非由性工作者組織,這樣的脈絡,使得「反人口販運」運動常使得性工作者二度受害。
反之,「原住民青年性健康網絡」(Native Youth Sexual Health Network)與「多倫多性工作者行動方案」(Toronto Sex Workers Action Project)結盟,促成「原住民性工作者外展與教育方案」(Aboriginal Sex Worker Outreach and Education Project)。這是一個尊重女性選擇(pro-choice)、也是加拿大第一個由原住民女性自己運作、服務原住民女性的方案,而不會只告訴女性如何脫離性產業。從我自己的經驗來看,我知道那樣的工作取向是沒有用的。
(圖片來源)
我認為政府將「反人口販運」包裝成捍衛女性權益的形象,是很危險的。人們不僅應起身對抗這樣的操作,也要重新思考主流文化對性工作的誤解。這些誤解影響著全世界的原住民女性。MTV EXIT(EXIT:End Exploitation and Trafficking,終結剝削與人口販運)正是一個赤裸裸的例子,解釋全世界的原住民女性如何被影響。MTV EXIT受聯合國愛滋規劃署(UNAIDS)等機構贊助,到許多被認定有「性販運」(sex trafficking)的國家,展開拯救女性的行動,使得許多原住民女性因從事性工作而被逮捕。西方的「反人口販運」陣營以捍衛人權之名,侵害她們的生活。
問:如果以刑罰禁止性工作不是解決方法,那麼,什麼是更有意義的、爭取公義的方式?
Jessica Yee:重要的是要與性工作者站在一起、一起工作。再者,我們必須促進人們更願意討論性與性慾。缺乏這些對話,人們難以深入販運與剝削議題的核心。
我們必須更坦然地討論性、性慾、與性工作。這些話題在原住民社群中,特別是禁忌。這是因為殖民政治對原住民的影響太大了。如果一個人被奪走他最強大的能力,他們的性慾也會一併被奪去。這正可解釋,何以我們社群中有些成員會混淆販運與性工作此二概念,並認為性工作對女性很糟。我們活在一個「倖存」的架構中,勉力維持社群的團結、捍衛社群免於暴力的威脅,過程中因為太少人協助原住民了,所以一旦有人幫助我們,我們就對現實的分析就失準了。
還有好多需要討論的東西。例如,青少年與性剝削的議題。即使在性工作者自己的運動中,人們傾向否認青少年有從事性工作的權利。我建議大家可以去認識芝加哥的「青少女培力方案」(Young Women’s Empowerment Project),這是個由13-24歲從事性工作的年輕女性組成的組織。她們最近產出了一個令人驚艷的研究報告,或許可以回應「什麼是更有意義的、爭取公義的方式?」這個問題。她們認為,人們應該先閉上自己的嘴,去聽聽那些實際受到政策影響的人的意見,尊重她們的看法。人們應當肯認:身為性工作者,有太多地方是不安全的;釐清構成販運與剝削的真正成因。最重要的是,人們應當被教育:對自決(self-determination)的尊重,不僅限於土地使用,更包括對我們自己的身體。
【2014/7/29更正】
感謝網友 Chun-Yu提醒,原文第三問「若不將女性為人口販運被害人,我們如何對抗性產業對女性的剝削?」之後的段落中,將decriminalization誤譯為「反歧視」,然實應為「除罪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