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誌》:幫助街友的一份雜誌?/《社企是門好生意?》書摘
編按:
時報出版於今(2018)年 11 月出版 《社企是門好生意?社會企業的批判與反思》一書,作者徐沛然用批判之筆,深入社會企業的本質進行剖析,並提出質疑:「將社會問題商品化,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甚至可能僅是靠著社會問題來營利。」
他在書中就社會企業此一概念提供更具歷史性、社會性的批判分析,並探討國內外案例。藉此帶領讀者,重新評估社會企業的效應,並思考公益這條路該指向怎樣一個未來。本篇選自第 4 章「《大誌》:幫助街友的一份雜誌?」徐沛然透過深受臺灣年輕人歡迎的《大誌》(The Big Issue)雜誌,探討社會企業將社會議題商品化後可能衍生的問題。原文超過 12000 字,NPOst 限於篇幅僅摘錄其精華。
另,本文原標疑似捲入過多讀者情緒與對立使後續討論失焦,為免長久之後搜尋頁面中持續出現,遂將本篇標題改為原書中的標題。
臺灣《大誌》(The Big Issue)目前為月刊形式,其運作方式是由大智文創甄選並培訓街友成為正式銷售員。新加入的銷售員可以獲得 10 本免費的《大誌》,之後向大智文創以一本新臺幣 50 元現金購買《大誌》,再以新臺幣 100 元的定價轉賣給民眾,進貨價與定價的 50 元價差就是銷售員的收入。在草創初期,《大誌》僅在臺北市各捷運站安排販售點,隨著業務與規模成長,如今販售點分布於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新竹市、臺中市、雲林斗六市、嘉義縣市、臺南市、高雄市、屏東市等縣市。除了在捷運站、火車站等乘客出入地點外,也包括了一些百貨公司、商圈等購物人潮較多之處。
此外,《大誌》本身設定的主要讀者是 20 至 35 歲的年輕世代,因此也在一些大專院校附近設置販售點。銷售員銷售時須身著《大誌》的識別證、印有《大誌》商標的橘色背心、帽子以及側背包。為了避免紛爭,每位銷售員均被分配到一個特定販售點,不可自行變更販售地點或者侵占到其他販售員的販售點。每個販售點均有特定的販售時間,銷售員需在規定的販售時間至販售點販賣《大誌》,此外也禁止在販賣《大誌》時同時賣其他商品。(註 1)
表面批發實際淪為僱傭,從中節省成本
在勞動法實務中,會從以下幾點特徵判斷雇傭關係,「人格從屬性」、「經濟從屬性」以及「組織從屬性」。人格從屬性指的是,勞工在工作時服從雇主權威,聽從其指揮監督,接受獎懲,以及遵守雇主所訂定的包括工時、場所等勞動規則。經濟從屬性則是指,由雇主提供場地、設備及相關材料,而勞工則為雇主勞動以換取薪資。組織從屬性指的是勞工被納入公司的生產體系中,並與同事分工合作。那麼,問題來了,《大誌》的銷售員跟《大誌》,也就是大智文創公司之間的關係是什麼(註 2)?

圖/Jordan Rowland@ unsplash
根據臺灣《大誌》創辦人李取中接受採訪時的說法,臺灣《大誌》採用批發,而非聘用或拆成的方式和街友合作。也就是說,他認為銷售員只是單純向《大誌》批貨來賣,賺取價差,如同商品批發商和零售商的關係。然而,如果彼此之間只是批貨的關係,《大誌》對於銷售員就應該沒有任何指揮監督的權限。就像是水果零售商向批發商買了 10 斤香蕉,這 10 斤香蕉要怎麼賣,批發商都不會、也沒有插手干涉的餘地。然而《大誌》的銷售員則不然。《大誌》對銷售員有著各種強制的工作規則,包括販賣的時段、地點、穿著、價格、方式等。如果違反規則,還可能遭受懲處,失去販售《大誌》的資格。這些做法都顯示《大誌》行使了身為雇主的指揮監督權。
儘管《大誌》可能會主張銷售員並非領取薪資,而是賺取售價差額,因此雙方並非雇傭關係。但根據最高法院 81 年臺上字第 347 號判決中表示:「又基於保護勞工之立場,一般就勞動契約關係之成立,均從寬認定,只要有部分從屬性,即應成立。」在過往的勞資爭議的案例中也多次確認了這個原則,雙方是否為雇傭關係不是由資方單方面認定,得透過檢視實際的互動內容而定。也就是說,只要確認《大誌》確實對銷售員行使了身為雇主的指揮監督權,那麼法院很可能會判定雙方實質上是雇傭關係,而非《大誌》對外宣稱的批發零售關係。

圖/Solent Creatives @ flickr, CC BBY 2.0
如果說,《大誌》的銷售員是被僱用的勞工,那麼他們的勞動條件應該要符合《勞基法》的規範,包括基本工資、勞工保險、健康保險和提撥勞工退休金。但很明顯的是,《大誌》並沒有盡到上述的雇主責任,因為他們宣稱《大誌》和銷售員之間不是雇傭關係。依照《大誌》公布在官網上的平均販售時間計算工時,以目前基本工資估算 100 位銷售員的每月平均薪資約為新臺幣 16,800 元,再加上雇主須負擔的勞健保、勞退雇主提撥等,如果《大誌》正式僱用這些銷售員,每個月所花費的人事費用平均每一位大約是 2 萬元。相較於目前銷售員的平均收入 15,000 元,《大誌》每個月將再多支出 50 萬元。(註 3)
沒有雇傭關係,沒有基本工資保障、沒有勞健保等影響是巨大的。如同我們前面所提,銷售員的收入完全來自於賣出的雜誌數量,而賣出的雜誌數量卻又取決於許多因素,以至於並非人人都能靠賣《大誌》維生,這就是為什麼基本工資重要的緣故,基本工資保障了勞工付出勞務之後,能夠獲得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然而《大誌》創辦人李取中卻在受訪時表示,如果採用聘僱的方式可能無法逐漸降低銷售員對外界的依賴度,同時也不能透過自食其力的過程去建立起自己的自信心。

圖/José Martín Ramírez C@ unsplash
為什麼李取中認為有穩定薪資的雇傭關係會增加依賴?過往許多研究均指出,對街友來說,一份穩定的收入是改善生活的重要起點。也許李取中認為,街友如果領薪水但不認真賣雜誌,就會造成《大誌》虧損。因此與其給薪資,不如讓他們「批貨販售」。銷售員如果不努力賣雜誌,不努力幫雜誌社賺錢,就不會有足夠的收入維生。至於那些被淘汰掉,賺不到錢、沒有辦法成功建立自信的街友,看來也不關《大誌》的事,畢竟《大誌》不是慈善事業。
這樣的做法目的是確保《大誌》的獲利,而非以保障街友生存為首要考量,卻能透過話術包裝成是要讓街友能夠「自食其力」。歷年來在臺灣討論基本工資的時候,總會有資方團體代表主張廢除基本工資,回歸市場機制。其對外說法大多是增加效率、或是刺激勞工競爭成長等,打的算盤不外乎就是要透過廢除基本工資以省下更多的人事成本。我們可以發現,李取中的想法不僅和資方團體如出一轍,他更以實際行動迴避了雇傭關係,取消了銷售員本應受法律保障的勞動條件。
究竟是街友需要《大誌》,還是《大誌》需要街友?
幾年前,我曾經在一個大學的課堂上,針對社會企業主題發表演講。教室中坐了近百位關心社會議題的大學生和研究生。當時現場調查,聽過《大誌》的人占了總人數一半以上,曾經購買過《大誌》的人約有 20 多名。如此高的比例,顯見這群年輕學子正是《大誌》鎖定的核心讀者;且曾經購買過《大誌》的人當中,大部分人未來都願意繼續購買《大誌》。然而,當我追問如果今天《大誌》跟街友沒有關係,不是透過街友販售,而是和其他雜誌一樣在便利商店上架販賣,還願意購買《大誌》的人有多少?原本將近 20 隻舉起的手紛紛放下,只剩下 1、2 隻手孤單的持續高舉,可見《大誌》的銷售高度仰賴街友作為招牌和通路。
那麼,問題又來了:究竟是街友需要《大誌》,還是《大誌》需要街友?

圖/Jonathan Rados@ unsplash
平心而論,賣《大誌》當然是街友的收入來源之一,如果販賣的地點熱門,自己又能適應良好,確實可能賺到足以維生的報酬(不過勞健保得自己想辦法)。根據行政院衛生福利部所公布的資料, 2016 年底,全臺灣遊民人數為 8,984 人。而《大誌》目前的銷售員大約百位,僅占了全臺街友人數約 1.1%。如果今天沒有《大誌》,確實會有一小部分街友少了主要收入來源,得依靠打零工或派報社等其他收入支持,生活得更辛苦。但如果今天《大誌》不再依靠街友販售,少了街友的活招牌,沒有了「幫助街友」、「社會企業」等光環,《大誌》的銷售量恐怕將一瀉千里,甚至可能面臨倒閉危機。這樣的效應,與其說街友需要《大誌》,不如說更像是《大誌》不能沒有街友。
然而,從創辦人、員工、媒體、學者還有社會企業推廣者,所有的說法都在告訴我們,《大誌》這類的社會企業在幫助街友,給弱勢群體工作機會。但我們反過來想,這份工作的勞動條件惡劣:收入微薄(大部分人月入一萬元上下)、不穩定、沒有勞健保、風吹日晒雨淋、要躲警察、偶而還得自己付罰單。一般勞工其實不太會願意接受這樣的工作。而看準了弱勢族群沒有太多選擇和議價的能力,提供低於合理標準的勞動條件,省下了大把人事成本,賺進鈔票與美名,這麼做就算是「幫助弱勢」的社會企業嗎?
客觀的說,經濟活動本就是互相依存的關係,雇主需要勞工提供勞務以生產商品或服務;勞工需要透過出賣勞力賺取收入。而將企業僱用勞工的行為片面描述成資方對員工的恩惠與幫助,這是資方的觀點,也是絕大部分社會企業所闡述的角度。

圖/Akshay Paatil@ unsplash
如果我們同意這樣的說法,那麼市面上僱用中高齡 2 度就業婦女的清潔外包公司,也算是社會企業了。即便我們知道,清潔公司僱用大量中高齡勞動者而不是剛畢業的社會新鮮人,只是因為他們更可能會接受這種低薪、高工時、繁瑣以及沒有升遷機會的工作崗位。
甚至我們還應該要為全臺各大小派報社平反,早在《大誌》開始「幫助」街友之前,派報社就已經不斷提供各種領日薪的工作機會給街友。視景氣而定,一天 600 至 1,000 元的收入,對許多街友來說可能比起賣雜誌更加穩定。不管是送報、發傳單或是路邊舉牌,幾十年累積下來,派報社所幫助的街友或弱勢勞工多不勝數,社會企業的頭銜,派報社可說是當之無愧。順著這個邏輯,我們可以繼續無限制的推導下去,直到所有曾經僱用或給付報酬給弱勢群體的公司全部都變成社會企業為止。
這就是我們在看待一個組織「僱用弱勢群體」的時候,不能不去分析其動機、提供的勞動條件、組織所付出的成本及努力等面向的原因,否則我們難以區分這個組織究竟是「幫助弱勢」,還是「利用弱勢」。

Photo by Matt Collamer on Unsplash
如果社會企業真的想要幫助弱勢,而不是像一般營利企業一樣用惡劣的勞動條件僱用弱勢,那麼勢必要投入額外的資源與成本,例如更完善的職業訓練與支援體系、更好的勞動條件等。但這麼一來,就又會和社會企業的營利目的相互牴觸。社會企業家學院的執行長阿拉斯塔爾‧威爾森也坦承,一個真的想要幫助弱勢或是改善問題的組織,勢必得比一般企業付出額外的成本和資源,或者其服務的對象本身經濟狀況就不佳,以至這些組織大部分都難以靠商業模式獲利。簡言之,如果真的想做好事,就很難賺到錢。
殺出紅海,臺灣《大誌》的成功策略
因網路及數位媒體的崛起,臺灣雜誌出版產業近年來遭受嚴重衝擊,發行的雜誌種類與發行量均大幅縮水。然而,創刊於 2010 年的臺灣《大誌》,在雜誌出版產業正值嚴酷寒冬的時候加入市場,反而逆風高飛,交出一張漂亮的成績單。
臺灣《大誌》創辦人李取中在 2012 年接受訪談時曾表示,臺灣《大誌》在正式發行一年半之後即達到收支平衡,這個進度比起各國《大誌》要來得快。甚至在 2016 年時,臺灣《大誌》每期銷售量就已經成長到 3-4 萬本,顯示當時《大誌》每一期的發行量最少都在 4 萬本以上,約為當年臺灣定期出刊雜誌平均發行量的 4 倍。

Photo by Charisse Kenion on Unsplash
相較於其餘雜誌出版同業的表現,《大誌》在出刊短短幾年內取得的成就驚人,顯見其商業模式必定有獨到之處。我們大致可以歸為以下幾點:
1. 放棄傳統通路的直接銷售法
臺灣《大誌》自從面市以來,就強調《大誌》主要透過自行招募培訓的銷售員販售,而不走一般雜誌在便利商店、書店上架的傳統通路。(註 4)雜誌如果要在便利商店上架販售,每一期都要先付一筆數十萬元不等的上架費,此外,每一本雜誌售出,都還要再跟便利商店通路拆帳,各分店過期未售完的雜誌也需由雜誌社全數收回。因此對於雜誌出版社來說,並不期待在便利商店上架能夠賺多少錢,走便利商店通路最主要的目的在於提升曝光度、衝高發行量,並以此為籌碼爭取更多的廣告刊登、增加廣告收入。
然而,在平面媒體逐漸式微的當前,平面媒體所能分到的廣告份額逐年下滑,雜誌的廣告收入也大幅縮水。相較之下,《大誌》的主要收入為雜誌銷售,廣告僅占《大誌》收入約 2 成,有效避開了仰賴廣告收入的風險。此外,銷售員預先和《大誌》購買雜誌是當場使用現金支付,而如果透過便利商店通路,往往要等到下一期,通路結算完成過後才會一次支付雜誌販售所得。因此不走便利商店通路,不僅能省下大筆上架費,每個月能立即收到的大量現金,更增加了公司資金調度的靈活與彈性。
2. 表批發、實雇傭,成本外部化
一般來說,自創通路往往意味著高風險,以及大量的前期投資。此時前面分析過的銷售員「表批發,實雇傭」的管理模式,不僅為《大誌》省下大量本應支付的人事成本,減少了財務上的壓力,不僅不須支付銷售員薪資及勞健保等,也能大幅降低《大誌》在拓展新的銷售點時的擴張風險。《大誌》可以迅速地擴張其販售地點和銷售員數目,而無須擔心人事成本飆漲。除此之外,不同於一般商品展店,《大誌》的販售點都是公共場所的路邊、騎樓、人行道或是捷運站口,不需要支付任何的場地費、租金或是水電網路費。
也正因為《大誌》設立的新銷售點幾乎不會增加其固定成本(註 5),所以《大誌》可以盡情將販售點設置於人潮商機匯集之處。雖然侵占公共空間營利是違法行為,但又因為《大誌》將所有違法的成本(罰單),全部都轉嫁給銷售員自行承擔。可以說,《大誌》所採用的商業模式透過在公共場所違法販售雜誌,然後將違法成本外部化,得以增加獲利。

Photo by Jonathan Kho on Unsplash
3. 社企光環,媒體幫抬轎
《大誌》身為臺灣知名社會企業,以幫助街友為賣點,自創刊以來,各媒體的報導絡繹不絕。媒體報導帶來的大量曝光,為《大誌》打出了知名度,省下了鉅額的廣告費用,這是一般雜誌所難以享有的待遇。此外,銷售員穿著《大誌》的背心在街頭兜售,沒有拿薪資,也沒有另外收取費用,相當於免費幫《大誌》當舉牌工。
以一般派報社路口舉牌工一天 600 元至 800 元的收入來看,全臺 100 多位現身於人潮密集處的《大誌》銷售員,不僅替《大誌》創造了極高的廣告效益,也為大誌省下不少行銷成本。
4. 熱情志工,填補人力需求
自創刊以來,《大誌》就積極培訓各種志工,其中包括在街頭和銷售員一起販賣雜誌並發送宣傳單的活動志工、在各大專院校辦活動推廣《大誌》的校園推廣志工,以及在《大誌》各發行站服務的發行站志工。各種類型志工的參與和投入,可說是對《大誌》貢獻良多。
然而,《大誌》作為一個營利事業,使用志工這件事本身存在爭議。特別是工作站志工得排班到場,還要負責銷售員補貨等常態性庶務,更像是以志工頂替了原本應該支付薪資的工作崗位。但在《大誌》身為社會企業、幫助街友的名義底下,似乎沒有人覺得這種做法有問題。大量地運用志工,使得《大誌》能夠以極低的成本辦理各種宣傳活動,維持發行站運作,這是一般雜誌出版商沒有辦法做到的事。
綜上所述,我們認識到《大誌》發展出一套非常成功的商業模式,極大化地利用了社會企業的光環,以及讓街友成為銷售員所能帶來的各種優勢。以致於《大誌》能在短短數年之內就逆勢成長到如今的規模。然而我們也可以看到,《大誌》的競爭優勢同時也建立在未經許可擺攤、疑似「表批發,實雇傭」、成本與風險外部化、免費志工人力等有違法之虞,或是倫理層面有爭議的做法之上。如果因為正式僱用街友,繳納罰單,合理租用場地、請兼職人員管理發行站,就會因此虧損,甚至無法持續經營,這樣的商業模式難道不是打從一開始就不應該存在嗎?
如同一般的未上市企業,臺灣《大誌》沒有公開其財務報表,所以我們無從得知從 2012 年收支平衡至今,臺灣《大誌》在銷售量持續成長下,創造了多少收益,而這些收益又如何被分配使用。
《大誌》商業模式的核心是街友及弱勢族群擔任的銷售員,因為有這群銷售員,《大誌》才能享有社會企業名號所帶來的各種名聲及好處,並將其轉化為自己商業競爭上的優勢。然而,臺灣《大誌》所做的卻僅僅只是「提供打工機會」給街友,並未投資更多資源在他們身上,甚至不願意承認彼此的雇傭關係,而讓銷售員自行吸收各種風險與成本。持平而論,剝下社會企業的華美包裝後,臺灣《大誌》和派報社之間有何差別?
被商品化的社會議題,將街友的需求簡化
包括創始的英國在內,世界各國的《大誌》通常會另行成立基金會,再由基金會協助販售員解決生活上食衣住行各方面的問題。然而,創刊於 2010 年的臺灣《大誌》,號稱一年半後就達到收支平衡。但直到目前(2018 年)為止,都還沒有依循相同模式成立扶助銷售員的基金會,僅是不斷地說服社會大眾購買《大誌》就等於幫助街友。
當原本應屬於公共領域的社會議題被商品化之後,對社會議題的關注與行動,就從制度面和結構面問題被轉化為消費選擇問題,「社會企業」的光環更讓我們相信購買商品就等於解決社會問題。然而街友面臨的困難是什麼?製造街友機制是什麼?街友的需求是什麼?應該提供的協助是什麼?這些問題都被簡化為「購買《大誌》等於幫助街友,所以賣出越多的《大誌》,就有越多街友被幫助」。
《大誌》讓我們將對於街友的關注,直接導向購買與消費,而非對公共政策的探討。但如果真正在乎街友議題,就會知道建立更完善的社會安全網才是關鍵,而不是將力氣放在賣出更多《大誌》。這就是我們前面所談到,社會企業將社會議題「去政治化」的效應。
註解
註 1:因各國《大誌》的經營型態不盡相同,除非特別註明,否則本章所指稱之《大誌》均為臺灣《大誌》。
註 2:《大誌》是雜誌,大智文創是發行《大誌》的公司,為方便讀者閱讀,本章中提到大智文創時多以《大誌》代稱。
註 3:根據《大誌》官網「販售場所」頁面所得出的銷售員平均工時約為每週 30 小時,但這樣的估算並不精確,因為銷售員實際上有可能遲到早退,也可能早到晚退。此外,一些銷售員每日工時超過 8 小時的加班費,以及假日工資都沒有計入,甚至有部份銷售員的工時超過《勞基法》所規定的上限。所以一個月會增加 50 萬元人事成本的數字恐怕還是低估。
註 4. 僅創刊初期曾經在便利商店上架,但短暫嘗試過後便迅速取消。
註 5. 當然,《大誌》需要設立各區域的發行站以便管理一定範圍內的銷售點,且便於讓銷售員補貨。但這方面的成本支出恐怕還是遠少於《大誌》商業模式在擴增銷售點和銷售員方面能省下的費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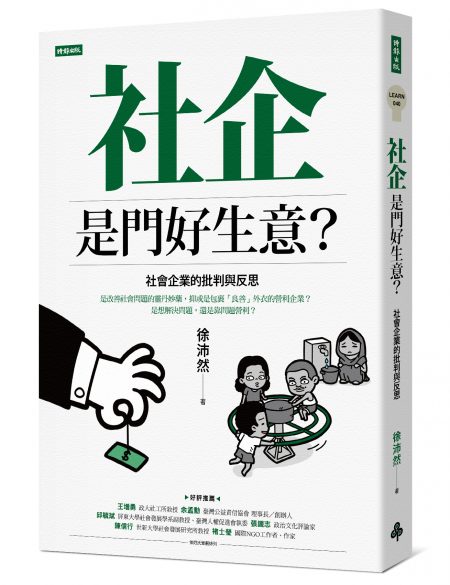
延伸閱讀:
海嘯之後,社會企業是否能帶領我們前往應許之地?/《社企是門好生意?》推薦序(余孟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