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青專欄/私娼的苦日子,但求一個溫柔的對待
我喜歡吃粽子,但在認識這些私娼以前,我都只吃肉粽。畢竟口味又重又過癮,當正餐吃著。反倒少吃那種傳統的,還要沾糖吃的鹼粽。因為已經吃飽了,也就將鹼粽繼續冰著。算是另類的挑食。
我到那裡的時候,只剩下一整排荒廢蒼涼的落寞。沿路的貨櫃屋已經嚴重鏽蝕,檳榔攤和崗哨亭的玻璃都已經破裂,地面冒起雜草。這裡離最近的交流道還要開上 15 分鐘以上,現在是一排已經廢棄的建物,我到的時候是夜晚。旅社門口坐著一排濃妝豔抹的私娼。我就提著行李在這個旅社住下。
這個工地位置現今看來極為偏僻,但這些廢棄的貨櫃屋過去曾經是國道施工期間的工務所,據說那時候整條省道都是人。司機們來到此處,會停車下來吃飯、用餐,那時候還沒有行動電話,大家都要提前來到工地門口排班等著卸貨或是待命。那時候的臺灣景氣正好,這些勞工一擲千金。整個國道施工期間的工人絡繹不絕,機械和車輛的聲音從沒停過。修國道的時候,也同時修省道。大大小小包商群聚於此。
這些偏僻的房舍就是那時候建起來的,原先只是提供中華顧問的工程師住,房間隔成一間一間。那時候的工程師地位極高,都有獨特的隔間,後來成為旅社。旁邊一樓的民房則保存著許久未更新的伴唱卡拉 OK 和沒插電的芭樂臺、格鬥天王等遊戲機,店門招牌已經泛黃,上面的字全部模糊了去,只用簽字筆醜醜的寫著炒牛肉豬肉炒麵炒飯。現在只剩這攤,以及另一個早餐店在營業。另一家雜貨店相隔 50 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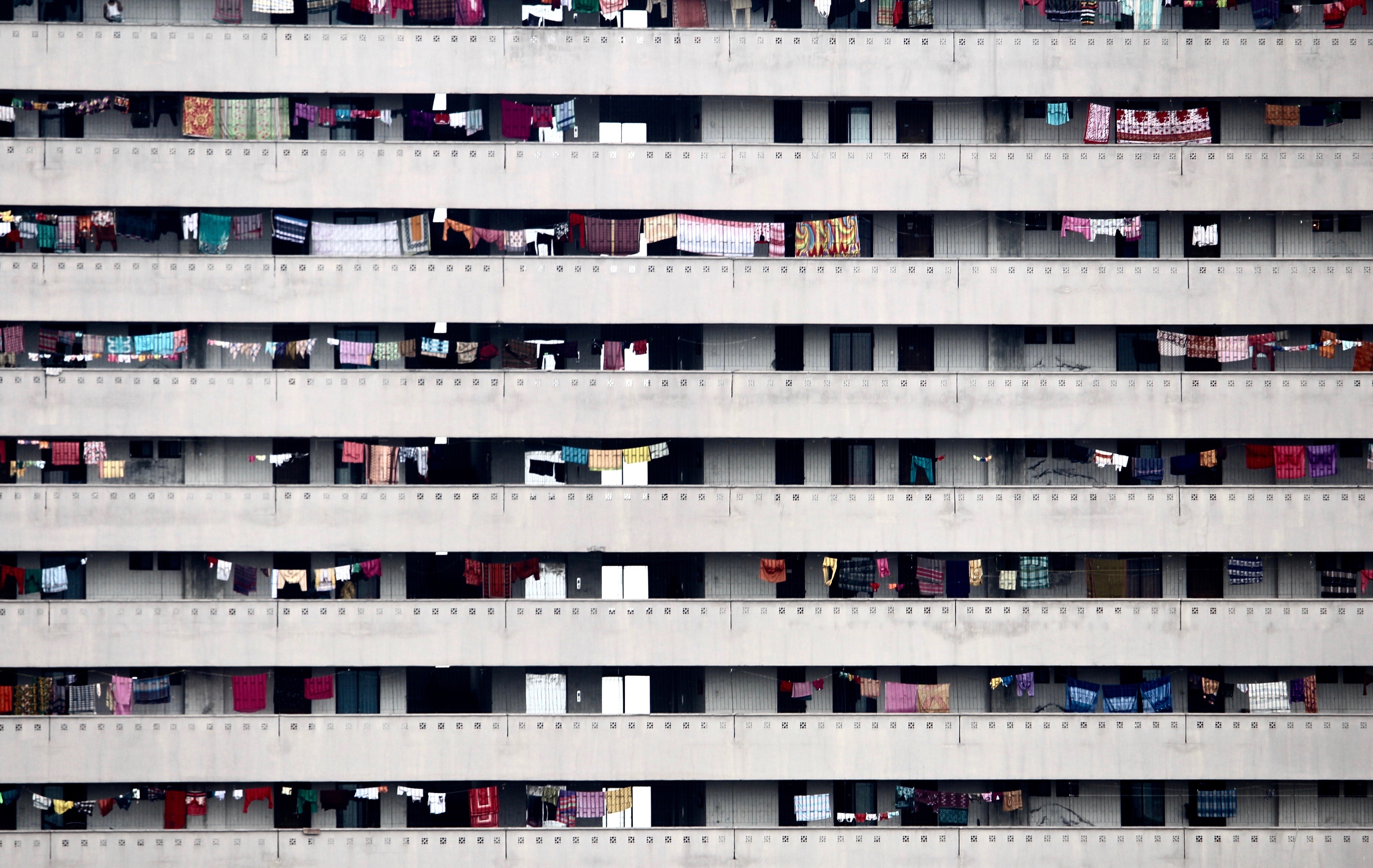
阿霞姐告訴我,這裡曾經很繁榮,那時候的客人們年輕力壯,在領到薪水後就前來,到小吃攤買春,到快炒貨櫃買醉,到這裡買一個小姐過夜。那時這裡很繁榮。她年輕的時候在這裡待過幾個月,接著到處去其他地方。私娼不可能、也不可以總待在同一個地方。因為長時間待下來的私娼會失去新鮮感,但換地方時總還能被這些店家雞頭稱為新貨,皮條客特別喜愛這樣推銷自己旗下的小姐。從她們的閒聊中也得知,過去如果在一家店待久,名聲傳到管區那裡去會有麻煩,身在公門好修行,夜半白嫖是福利。
但她最後回到這裡,在這裡住下。因為她已經夠老。她的年齡比我母親還大得多,實際上應該稱為大姊。也因為這個原因,實在沒有機會再多賺一點錢了。樓上有一個房間是她的,我知道有另一個小姐也有這樣一個房間,那時她就已經超過 50 歲。
我來到這裡的第一個週末,對於這裡的雙槽洗衣機實在無法上手。她好心教我用了一次我還是不會。所幸乾脆撒嬌請她幫忙洗。她倒是很快樂的應聲說好。之後我在那裡住下半年,都是她為我洗衣。那時工地做的是露天開挖,那些我脫下就不想再穿起來的衣服她會為我浸泡,接著用腳踩,隔天後再放入洗衣機,洗完晾乾,一件件摺好放在我房間門前,每週僅象徵性意義的收我兩、三百。

旅社老闆已經過世,現在管店的是老闆娘和她的女兒。老婦人終日在對街新房子一樓內看電視,阿霞她們這些小姐告訴我,老太太會念她們簽六合彩和樂透。管事的女兒負責前來收房租,我的房間一個月四千,包水包電包冷氣。要是壞了什麼燈泡堵了水管,就等她丈夫晚上回家再前來修理。有時候,小老闆娘,也就是這女兒會跑來找這些「小姐們」,告訴她們有什麼摺蓮花、包粽子、做香包或摺紙盒的工作。
我的房間其實是最好的一間,即使廁所裡沒有燈也沒有門,但確實是最大最好的一間。因為有電視和一個書桌,所以師傅們特別留下這房間給我,能辦公還能看電視。只是這旅社是多年搭建而成,實際上分成前棟後棟,我們往往從後門進出,前門留給小姐們接客。只是當我在洗澡時,也總還是能聽到從浴室管道傳來的、這些小姐的職業服務,從稱讚好大好強要死了,到叫春中的制式,規律,誇大並且浮誇,都是她們專業的一環。有時經過她們,還會抱怨起現在男人們看了 A 片後,自以為是的鬼叫和炫耀。

我的工人師傅們分為兩類,年輕的寧願開車上國道,開半小時前往小姐較年輕的店家消費,另一些年老的則與這些小姐年齡相近,住下來的同時也就在入夜後將之招來房內。這裡的行情是 600 或 800,過夜則要 2000,但相處久的似乎算起錢來也就亂七八糟了。阿霞會在中午時去對面的熱炒店幫忙,然後回來休息睡午覺,下午再出來梳洗整理後等著晚上接客。伴唱小吃店阿公店和妓院的界線其實在這裡沒有如此清晰,有時候這些小姐從晚上就在招牌亂寫的熱炒攤,和客人嬉鬧著吃完飯後上樓辦事。有時過夜也有時結束後就離去。但從我手下工人們的話中,似乎這樣的溫飽思淫慾一條龍的客製化服務很「划算」,我猜想也就是這些小姐們給了折扣,又少賺了些。
這些大姊們住在這裡,也因為這裡有著奇特的氛圍,特別對她們包容而友善,中午時刻這些幫忙的小姐們往往隨意從攤位上揀自己要吃的,隨意煮隨意吃,從不見熱炒攤的老闆夫妻們說什麼。這對夫妻沉默寡言。要到很後來我才知道這棟樓都是他們的,但他們也不對這些小姐從事的行業提出抗議或檢舉。我想是因為他們理解的比我深切,他們比我慈悲。

在那工地工作期間,其實還是必須往來臺北,休假、交代辦公事項、聯繫下一個案件並且確認投開標,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世界。我在中秋節前回來旅社,那時候正值颱風,晚上我到的時候旅社正要關門,畢竟沒有人會在颱風夜裡前來尋歡,我應時的拿出月餅,想和這些大姊們一同分享。她們倒是笑了起來,接著阿霞姐說:「哩乎姐呀過中秋,咱請你過肉粽節!」幾個大姊們從冰箱裡拿出有點硬的鹼粽,然後從冰箱和廚房裡挖出一連串的調味品:蜂蜜、豐年果糖、紅糖、白糖、花生粉、草莓果醬……
「哩嘴甜甜,乎哩呷這甜甜甜」我頓時感到受寵若驚,笑鬧一番。我是隔天到早餐店,才知道這些鹼粽是端午節時,小老闆娘接下的兼差,前來找七、八個大姊包鹼粽,完成後可拿三千。其中五個人包了兩天後,市場的攤販跑了。想當然錢沒拿到,這些粽子,也就在端午過後沒多久,一直等到中秋。
隨著工程結束,工人們紛紛先我離開。一個晚上,我逛了夜市後前往雜貨店,恰好與快炒店攤聊起,才知道阿霞是養女,15 歲被嫁到臺中工廠,那時的臺灣習慣用女人當公司負責人、用女人的名義開票。當年的政府只要發現跳票就抓人去關。阿霞 19 歲入獄,出獄後夫家已經人間蒸發,但身上仍有不知道從哪裡來的債務,對這樣沒有家人的女性,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從地獄中垂下蜘蛛絲,誘逼她前往特約茶室自立自強。她沒有離開臺灣本島,我也至今不知她是去了臺北還是哪裡的 831,只知道她的人生從此過著被追債、逃離、再被追債、再逃離的生活。
聽完這故事我感覺心裡一沉,經過旅社時阿霞她們幾個大姊們正在門口,將剩飯集中拌勻後倒給路邊的流浪小狗,她怕傷心,堅持不給狗取名字,只知道有這些狗兒會前來要飯。

其他大姊們的故事大同小異,有的和阿霞一樣,有的是被男人所騙,有的也是所嫁非人。她們多半單身。即使還有家人往來的,也都極力讓工作的地點遠離孩子,彼此之間似乎好像也有這種默契。然而她們總碎念著以前的日子難過,沒做多久就又怕遇上黑白郎君,只要被抓過,這些小姐大姊阿姨終身怕警察,又怕又恨的咒罵。他們手中的警察會白嫖,要試車。會在正氣凜然的領了乾股分紅後說是為了社會秩序。此時話鋒一轉,回頭自嘲現在人老珠黃,不再年輕美麗的好處是免去了警察們的騷擾。這些大姊們的人生就是如此,不知道哪裡有了問題,但一踏入後,就極難有機會轉換工作。
這個年齡的女人,既被傳統觀念綑綁,又被社會遺棄。對這個社會也不再存有希望,也不配得她們的希望。有些有了男友,也不願意再走入婚姻,畢竟法律是保護有東西可以保護的人。這樣的生命不值得社會憐憫,寧可就這樣的過下去,直到再也沒有對象。而我們對於這些女人就是歧視和漠視,少有的關注卻往往以獵奇方式窺探,既先入為主又嘲弄。在這社會上幸福並享有權利者,只要先定她們的罪,就不需要檢討自我在結構中的行為。兩千年過去,人們還是不知道曾有救世主說,人應該從被歧視者的身上回頭看清自己。
這些大姊們,現在就連自己的戶口也不知道在哪裡,也不需要知道在哪裡。這裡的人看病用同一張健保卡,騎同一臺機車。年老的好處是發現那些害怕又討厭的警察們現在看來都成了年輕又善良的孩子,對她們這樣沒有戶口、沒有駕照的老人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畢竟她們大概少有的快樂就是幾個人到處逛逛,有時候騎車,有時隨小老闆娘搭車去廟裡拜拜,祈求來生投胎男人免去苦難。更多時候會齊聚起來對樂透彩。但她們始終沒有得到庇護和救贖。在這種環境之中,諸神隱滅,基督未顯。我在這裡見到的,只有一個個被社會遺棄的人。

我的工地案子結束時,她們似乎非常不捨我們這樣的過客。這些工人雖說對話低級下流,但給錢豪爽並且毫無詭詐,住了四、五個月以來也都相安無事,工人們請客喝酒時,也不在乎她們賴過來包剩菜餵小狗,甚至偶有工地破銅爛鐵賣了也給她們吃紅……我們只是不開單,不警告,不恐嚇也不白嫖。最重要的是把她們當人,將拜拜的東西分享,逛完夜市隨手帶點飲料,僅僅如此而已。
我離開時,將多買的延長線、便宜買入的棉被和開車北上載不下、視為累贅的沐浴乳洗髮精全留給了阿霞姐,她握住我的手對我祝福:「你這樣好的人,未來會娶水某!你會賺大錢!你未來會好命的!」我至今仍認為阿霞姐的眼睛很美,皮膚很白,年輕時一定非常漂亮。她的眼睛又圓又大,眉毛細長,聲音細膩而溫柔。如果在現在,怎麼樣也會是個自拍會有上千人追蹤的正妹。但現實就只是如此。我臨走前她還在顧那些小狗,她對我的祝福,我至今仍認為我配不上,那是她才應該擁有的。
我在這工地之後總喜歡在夏天時吃鹼粽,用很多種沾料來吃。用蜂蜜、豐年果糖、紅糖、白糖、花生粉、草莓果醬沾著吃。那是她們教我的吃法,慢慢的,細細的,用不同的方法來品嘗。即使那時候吃的粽子已經久放,失去了新鮮,失去了彈性和應有的口感,但依然值得細細品嘗。
一如她們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