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世紀最重要的道德義務:人必須去「知道」各種事/《21 世紀的 21 堂課》書摘
編按:
你真以為有「自由意志」?還是改聽大數據和演算法就對了?我們該提防機器人,還是該提防機器人的主人?天然愚蠢遇上人工智慧,人類還剩下什麼能力勝過人工智慧?這些提問,顯然是 21 世紀的我們日日所面臨的課題⋯⋯
今年(2018)8 月底,天下文化出版了《21 世紀的 21 堂課》一書,作者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為全球新銳歷史學者,《21 世紀的 21 堂課》是他最新著作,探討著當前世界的重大課題。
本篇選自書中第 4 部的第 16 堂課〈正義:我們的正義感可能已經過時〉,哈拉瑞帶我們看見在這全球化的 21 世紀社會,對正義感的理解已經不同於以往,我們又如何在複雜的全球化世界,實現所信任的價值觀?
文/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
一如其他所有感受,人類的正義感也是從遠古演化而來。幾百萬年的演化過程,形成了人類的道德,很適合處理在小型狩獵採集部落中的各種社交和倫理問題。如果我和你一起去打獵,我抓到一頭鹿,而你空手而返,我該與你分享獵物嗎?如果你去採蘑菇,滿載而歸,但光是因為我比你強壯,我就可以把所有蘑菇都搶走嗎?
如果我知道你打算暗殺我,我可以先發制人,在暗夜裡一刀劃過你的喉嚨嗎?
如果光看表面,人類雖然從非洲大草原走到了都市叢林,情況似乎也沒什麼改變。有人可能會認為,我們今天面臨的問題如敘利亞內戰、全球不平等、全球暖化等,都只是過去的老問題規模放大而已。然而,那只是一種錯覺。「規模」本身就是個問題,而且從正義的觀點(一如其他許多觀點),人類已經很難適應現在的這個世界。

圖/Giammarco Boscaro @ unsplash
如何在全球化的世界實現正義?這其中的問題並不在於價值觀。21 世紀的公民,無論是有宗教信仰或相信世俗主義,都抱持許多價值觀。真正的問題是:如何在這個複雜的全球化世界裡,實現這些價值觀?這其實是個數字問題。長久以來的狩獵採集者在演化之下所建構出的正義感,能應付的是幾 10 平方公里範圍內、幾 10 個人的生活問題。想要把這套正義感應用到各大洲和幾百萬人之間,我們的道德感就只會當機故障。
想要追求正義,除了要有一套抽象的價值觀,還必須明確掌握因果關係。如果你去採蘑菇,要餵養小孩,我卻用暴力把整籃蘑菇搶走,這意味你的一切辛勞將付諸流水,你的孩子必得挨餓入睡,而這當然是不公平的。這件事的因果關係很清楚,也很容易理解。
但不幸的是,現代全球化世界天生就有一項特點:因果關係高度分化且複雜。例如,我可能就是靜靜待在家裡,從來沒傷害過任何人,但對左翼運動人士來說,我完全就是以色列軍隊及西岸屯墾區殖民者的共謀。在社會主義者眼裡,我過著舒適的生活,是因為我也共同奴役了第 3 世界血汗工廠裡的童工。動物福利提倡者則會告訴我,我的生活交織著史上最醜惡的犯罪事件:綁架了幾 10 億隻家禽家畜,進行大規模的屠戮剝削!

圖/Tim Marshall @ unsplash
這一切真的都該怪我嗎?這實在很難說。我現在的生存,需要依賴複雜到令人眼花繚亂的政經關係網路,而且全球因果關係盤根錯節,就連最簡單的問題也變得難以回答,例如:我的午餐來自哪裡、是誰製作了我穿的鞋,或是退休基金正拿著我的錢在做什麼投資。
如果是原始的狩獵採集者,會很清楚自己的午餐從哪兒來(自己採集的)、誰做了她的鹿皮鞋(那個人正睡在 20 公尺外)、自己的退休基金又在做什麼(正在泥地裡玩呢。那個時候,人類只有一種退休基金,叫做「孩子」)。
比起那位狩獵採集者,我實在無知太多了。我可能要經過多年研究,才會發現自己投票支持的政府,偷偷把武器賣給地球另一邊某個躲在幕後的獨裁者。但在我投入時間找出這個事實的同時,卻可能會錯過更重要的一些發現,例如我晚餐吃了蛋,但那些生蛋的雞現在怎麼了?

圖/Mai Moeslund @ unsplash
21 世紀最重要的道德義務:人必須去「知道」各種事
如今整個社會體系架構的方式,讓那些不去費力瞭解事實的人得以維持幸福的無知狀態,而想要努力瞭解的人則需要歷經諸多艱難。如果全球經濟體系就是不斷以我的名義、在我不知情的狀況下偷走我的錢,我該如何避免?不管你是要以結果來判斷行為是否正義(偷竊是錯誤的,因為這會讓受害者痛苦),又或覺得結果並不重要、該從「無上義務」(categorical duty,或稱「定然責任」)來判斷(偷竊是錯誤的,因為上帝這樣說),都不會讓情況有所不同。
這裡的問題,正在於情況已經變得太過複雜,我們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過去訂出要人「不可偷盜」這項誡命的時候,所謂的偷盜,指的是用你自己的手,去實際拿走某項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然而到了現在,如果要討論盜竊,真正重要的問題所談的,都是完全不同的情況。
舉例來說,假設我投資了一萬美元,購買某家大型石化公司的股票,每年得到 5% 的投資獲利。這家公司獲利極高,但原因是該公司躲避了外部成本,直接把有毒廢棄物排入附近河流,完全不顧對當地供水、公共衛生或野生生態可能有何影響。該公司財大氣粗,請了一大批律師,保護該公司不必擔心被告上法庭要求賠償,甚至還聘用政治說客,阻擋任何強化環保法規的意圖。

圖/Petar Petkovski @ unsplash
我們可以指控這家公司「偷了一條河」嗎?我的角色又是什麼?我從來沒闖入任何人家裡,也從來沒有從任何人的錢包裡拿錢。我並不知道這家公司是如何獲利,甚至都快忘了自己的投資組合裡有這家公司。那麼,我也犯了偷竊罪嗎?如果我們就是無法得知所有相關的事實,該如何才能說自己的行事都符合道德?
我們當然可以用「意圖的道德性」這樣的概念,來迴避這類問題──重要的是我的意圖,而不是我的實際行為或造成的結果。但在這個一切都緊緊相連的世界上,最重要的道德義務其實就是:人必須去「知道」各種事。
現代歷史最嚴重的罪行,不僅是出於仇恨和貪婪,更是出於無知和冷漠。然而,到什麼地步才算得上是「真誠求知」?現在回頭看 1930 年代的納粹德國,很容易就能對其中許多人的行為道德下定論,但這是因為我們已經知道整個因果關係鏈是如何串起。要不是有這樣的後見之明,或許就難有這樣的道德定論。但令人痛苦的事實是:對於仍停留在狩獵採集者時期的人腦來說,世界已經變得太複雜了。

圖/蔡 嘉宇 @ unsplash
世界上大多數的不公義,來自「大規模的結構性偏見」
當代世界大多數的不公不義,並不是來自個人的偏見,而是來自大規模的結構性偏見。但我們這種狩獵採集者的大腦,還尚未演化出能夠察覺結構性偏見的能力。每個人至少都會是某些結構性偏見的共犯,而我們就是沒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去發現這些事實。
為了寫這本《21 世紀的 21 堂課》,讓我有機會好好做做這項功課。討論全球問題的時候,我常常可能犯下的錯誤,就是只看到全球精英階層的觀點,而忽略了各種弱勢群體的想法。全球精英掌控了話語權,因此我們不可能錯過他們的觀點。相較之下,弱勢群體通常遭到噤聲,我們也就很容易遺忘他們;並非我們懷抱惡意,只是由於純粹的無知。
例如,澳洲塔斯馬尼亞島上的原住民有什麼獨有的問題、特有的觀點,我實在一無所知。甚至就因為我實在所知太少,在我所撰寫的《人類大歷史》的第一版裡,我還曾誤以為,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已經全部遭到歐洲殖民者掃除而滅絕。但事實上,目前還有成千上萬的人口,保有塔斯馬尼亞原住民的血緣,也面對著許多當地獨有的問題──其中一個問題就是:常有人誤以為塔斯馬尼亞原住民已經滅絕,就連研究歷史的學者不也犯了這個錯?

圖/Manuel Meurisse @ unsplash
而且,就算你本人屬於某個弱勢團體,對該團體的觀點有第一手的認知,也不代表你就瞭解所有其他弱勢團體的想法。所有團體或子團體,都會有些自己才會遇到的玻璃天花板、雙重標準、充滿暗示的侮辱,以及體制上的歧視。一位 30 歲的非裔美籍男性,對於身為「非裔美籍男性」擁有長達 30 年的獨到經驗。但是他仍然不會知道,當一個非裔美籍女性、在保加利亞的羅姆人(Roma,一般誤稱為吉普賽人)、眼盲的俄羅斯人,或是在中國的女同性戀者,會是什麼滋味。
在過去的年代,這個問題並不那麼重要,因為不論地球另一邊遇上什麼困境,你大概都不用負什麼責任。只要你看到鄰居發生不幸的時候,還能有點同情心,通常也就夠了。然而,今日像是氣候變遷和人工智慧之類的重大全球議題,對所有人都會造成影響,不管你在塔斯馬尼亞、杭州或是巴爾的摩,都無法倖免,所以我們也就該把所有人的觀點都納入考量。
但,誰真能做到?哪有人能夠搞清楚,全球各地成千上萬的群體所組成的到底是什麼樣的關係網路?

圖/Luiz Felipe Souza @ unsplash
如何面對龐大的道德問題?縮小規模或是拒絕面對?
就算我們有這個打算,多半也已經再也搞不清楚世界上有哪些重大道德問題了。如果講的是 2 個採集者、20 個採集者、又或是 2 個鄰近部落間有何關係,大概我們還能夠理解。但如果是幾百萬個敘利亞人之間、5 億個歐盟居民之間,又或是整個地球上所有群體和子群體之間的關係,人類就是無力理解。
面對規模如此龐大的道德問題,人類為了得以理解和判斷,有下列 4 種常用的方法。第 1 個方法是縮小問題規模:把敘利亞內戰,想像成 2 個人在打架,一個是阿薩德政權、一個則是反抗份子;或一個是壞人、另一個是好人。這樣一來,整個複雜的衝突史,就被替換成一套簡單明瞭的故事情節。
第 2 是把重點集中在某個感人的故事,用它來代表整個衝突事件,很多慈善機構長期以來對這種方法再熟悉不過。如果你搬出整套統計和精確的數字,想要向大眾解釋事情有多複雜,大眾只會失去興趣;但如果搬出某個孩子的辛酸故事,不但能賺人熱淚、叫人血脈賁張,還能讓人誤以為自己一定站在道德正確的一方。

圖/Tucker Tangeman @ unsplash
第 3 種方法是編出各種陰謀論。想知道全球經濟究竟如何運作、又究竟是好是壞嗎?這太難搞清楚了。不妨換個方式,想像就是有 20 位億萬富翁在背後操弄,控制了媒體、發動了戰爭,一切都是為了聚斂更多財富。
這類陰謀論,幾乎永遠都是一套毫無根據的幻想。當代世界就是太複雜,不僅難以明辨正義與公平,就算是想控制與管理,也是一大問題。不管是億萬富翁、中央情報局、共濟會或錫安長老會,就是沒人能真正搞清楚世界到底正在發生什麼事。(但也因此,並沒有人能夠有效操弄一切)
以上 3 種方法,都是拒絕面對世界究竟有多複雜。而第 4 種、也是最後一種方法,則是創造出一套教條,全心相信某種號稱全知的理論、號稱全知的機構,或是號稱全知的領導,然後無條件的跟隨。
宗教和意識型態的教條,之所以在這個科學時代仍然深具吸引力,正是因為它們提供了一種避風港,讓我們得以不去面對令人沮喪的複雜現實。而我在第 14 堂課〈世俗主義〉也提過,就算相信世俗主義,也無法避開這種危險。就算你打定主意要抗拒所有宗教教條、一心追求科學真理,遲早還是會因為現實生活太過複雜而不勝其擾,於是你決定造出某種教義,叫人別再追問下去。這些教義確實能讓人在智識上得到撫慰、在道德上感到安心,但這究竟算不算是正義,仍舊無法確定。

圖/Diana Vargas @ unsplash
我們該怎麼做呢?是要接受自由主義的教條,相信只要把力量交給所有個別選民和顧客做決定,就能得到最好的結果?還是要推翻個人主義的路,重新拾取歷史上許多文化的做法,把力量交給某些社群團體,走向集體共同判斷的路?
然而,這樣的解決方案只是讓我們從「個人無知」的刀山,走向「群體偏見」的油鍋。在狩獵採集部落、鄉間聚落、甚至是城市社區,都還有可能共同思考大家所共同面對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全球性的問題,而我們並沒有一個全球性的社群。不論是臉書、國族主義或宗教,距離要建立這樣的社群,都還有極遠的距離。所有現存的人類群體,都還只是一心追求自己的利益,而非理解全球的真相真理。不論是美國人、中國人、穆斯林或印度教徒,都無法建構「全球社群」,於是他們各自對現實的詮釋,也就都難以令所有人信服。
所以我們該放棄了嗎?人類會不會就是無法理解真相、不可能追求正義公平?我們是否已經正式進入後真相時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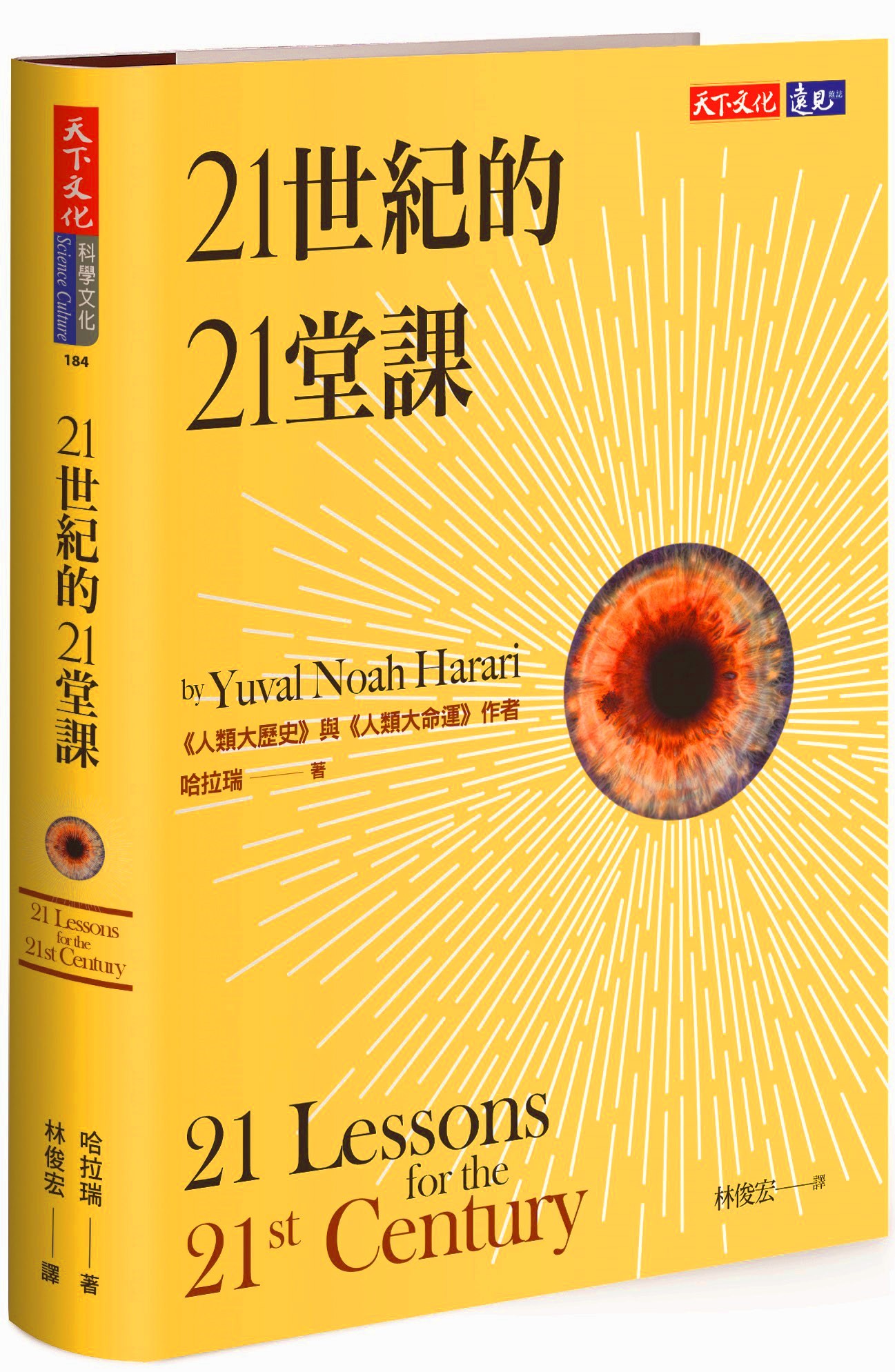
延伸閱讀:
陳岱嶺專欄/當志工親臨現場,就有義務揭露惡行嗎?談援助工作的策略性發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