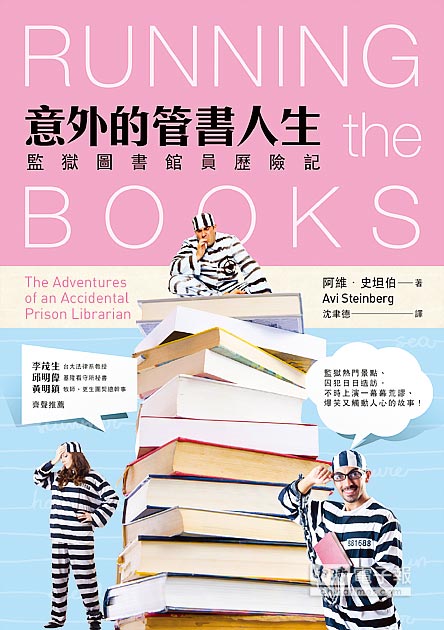「踏上臺灣土地的時候,卻是在監獄裡」,境外受刑人在「囹圄之城」的生命自處/《奴工島》書摘
編按:
寶瓶文化於今年 (2018 )10 月出版《奴工島:一名蘇州女生在台的東南亞移工觀察筆記》一書,作者姜雯深入田野蹲點,與移工訪談、書信往返,甚至探監,完成這本極具文學性的觀察筆記,書中透露臺灣種種荒謬與不真實的情節,卻是移工無盡的日常。
本篇摘自章節「囹圄城中城」,姜雯持續探監在臺灣的境外受刑人,並從多次的見面與書信中,勾勒出境外受刑人的心情與處境,以及在那蒼茫無邊,海上的遠洋漁船上的種種。
「我從來沒看過臺灣是什麼樣子。踏上臺灣土地的時候,卻是在監獄裡,這是天意吧。」
從外籍受刑人,而且是境外漁工口中聽到「天意」兩個字時,我有一些啞然。我不知道上蒼是如何來為我們這些藐茲一身的凡人安排命運,也許有些事,從一出生就註定好了,而有些事,卻是命途中的選擇。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只是,何為天堂,何為地獄?尤其在那蒼茫無邊,海上的遠洋漁船。
2017 年 6 月 21 日,我第一次去探望阿冀,在排隊等待時我有些緊張,思忖著會見到怎樣一張面容,該如何介紹自己,又該說些什麼。22 梯次,27 窗口,進入接見室大門後一路向右走。通道很窄,剛好容納一個人走路的寬度,右邊是牆壁,左邊則是探視窗口。窗口前已經整齊坐好了一排受刑人,清一色平頭、灰色囚衣,隔著玻璃窗和生鏽的鐵網與另一邊的親人朋友對望。

圖/Jeremy Bishop @ unsplash
我惴惴不安地走到 27 窗口,阿冀已經在鐵窗的另一邊了。34 歲的他看上去有些蒼老,頭髮稀疏,圓臉,戴著眼鏡,皮膚很白,五官不如其他印尼人那麼深邃,是中年人微微發福的體型。手上戴著紫色串珠,他的樣子很像在街口吃麵時常會遇到的,隔壁餐桌帶著孩子吃晚餐的父親。
當我在他面前坐下時,他左右張望了幾下,用一臉疑惑的表情望著我,彷彿是怕我搞錯了座位。我對他揮手微笑,表示自己沒搞錯。「嗶——」一聲長音後,我和他各自拿起面前的電話。我表明身分和來意,阿冀臉上的疑雲才消散,繼而轉為開心。
「罵人可以,不要打人就好了啊」
阿冀是境外漁工,在臺灣既無家人又無朋友,所以不會有人來探望。2016 年,阿冀因為和「和順才 237 號」案的帕瓦同家工廠,得知外面有個組織會幫助外籍受刑人後,便鼓起勇氣寫信給 TIWA (臺灣國際勞工協會)。他在信裡寫道:
我在監獄裡已經 8 年,我需要外面的支持和幫忙,特別是從印尼政府,因為我在臺灣沒有朋友和親戚。我曾經寫信給總統 Jokowi 先生,還有寄給印尼辦事處,但是沒有一點回音和反應。如果可以直接說,我們在這裡很可憐,我們需要支持和激勵,需要動力和指導,需要光明,給我們力量和忍耐經歷這個刑期。

圖/Eduardo Sánchez@ unsplash
有來自外面的人能會客總是開心的,阿冀和我講起最近的狀況,他換了工廠,裁縫課程這週就要畢業了,之後便能在工廠裡做衣服。他說自己在監獄第 9 年了,爸爸已經過世,兄弟姊妹也都不在家了,家裡只有年邁的媽媽和六弟。他中文不錯,講起話來客氣有禮,笑的時候也很收斂,牙齒才剛從笑容裡露出來,嘴角便又把它們收回去。
問到之前的案子,阿冀的神色裡立刻糅雜著憂傷、沉痛和憤怒,他說自己在香港工作,上的是臺灣老闆的漁船,老闆不但罵人,還打人。他強調了好幾次:「罵人可以,不要打人就好了啊。」
「工作非常累,還要被打、被罵就很生氣,」他一邊說一邊做著被打頭的動作,「第一次看到這樣的老闆,最後才做了衝動的事。」阿冀的語氣愈說愈激動,而我握著電話的手也愈來愈緊,生怕一鬆手,就會隨著他的記憶捲入海浪裡。

圖/Riddhiman Bhowmik@ unsplash
說完案子,我們都有些尷尬,沉默幾秒後我問他等下要做什麼,他說還能趕上 3 點半的裁縫課。我正想問他有沒有需要買點什麼,電話就猝不及防地掛斷了。阿冀的聲音消失了,剩下被嘈雜包裹著的沉默之聲。隔著鐵窗,他用手比劃寫字的樣子,應該是說會寫信給我,然後站起來和同一梯次的人向鐵門走去。我邊走邊朝他揮手告別,他很靦腆地笑著,走進去又回頭,直到我看不到灰色的囚服和他腳下的藍白拖。
回到會客大廳,我突然覺得熱浪襲來,才發覺原來裡面是那麼冷。也許是冷氣太強,也許是會客室的白瓷磚、鐵皮牆把暖意都吸盡。15 分鐘可以講的話很少,又因為時間限制,必須把對話的密度壓縮,那 15 分鐘也就因為緊湊而顯得迅疾。當我回歸到會客大廳的自由空氣中,時間的面容又慢慢舒展開來。
我抽了號碼牌,填了接見單,接著在會客大廳坐下等著見下一個受刑人阿森。

圖/Daniel Lerman @ unsplash
「在這個黑暗的監獄走道中,有一點光明照亮在我心中」
阿森和阿冀是同案受刑人,他們都是 2008 年以「強盜殺人罪」被指控的境外漁工,2 人的刑期都是 20 年。同案還有另一名境外漁工卡力,因是主謀被判以無期徒刑,到現在還是 4 級受刑人。根據北監的規定, 4 級受刑人的接見對象以親屬為限,因此漫長的刑期裡,卡力應該從未被探視過。況且作為境外漁工,從未踏上過臺灣土地,又怎能奢望有外面的人來探望呢?這又讓我想起阿冀寫給 TIWA,請求探視信裡的文字:「在這個黑暗的監獄走道中,有一點光明照亮在我心中。」
我無從揣摩卡力心中是否還存有光明和希望,TIWA 曾經透過公務會面見過他,他來自印尼中爪哇省(Jawa Tengah),已經 53 歲了,有 3 個孩子,而且他已經做阿公了,27 歲的大兒子也在做漁工。他說幸運回到印尼的話都 60 幾了,沒辦法工作了,不知道往後的日子要怎麼辦,現在只能每天禱告。案發時他已經 4 個月沒拿到薪水了,迫於養家的壓力才鑄下大錯。
我一邊遙想著在海上工作的樣子,卻無論如何也無法想像出那該是多麼窘迫的境況,於是我只能盯著登記窗口前的輸送帶,看裝著食物的五顏六色的塑膠袋緩緩被送去檢查。記得有次另外一名受刑人說想吃肯德基,但因為有生菜和沙拉醬而被要求當場挖掉,漢堡被送出來挖生菜前,就已經因為檢查而大卸八塊,最後的模樣慘烈無比。

圖/Kyler Boone@ unsplash
想著想著便輪到了我的梯次。26 梯次,27 窗口,很巧地和剛才的阿冀同一個窗口。進入接見室的門,我再一次被冰冷的空氣襲擊,白熾燈把心裡的忐忑照得通透。在同一個窗口坐下,阿森已經坐在那裡,當我與他對到眼時,他嘴唇微張,後來才知道原來是看到陌生人,被嚇到了。電話鈴還沒響起,在這之前,彼此沉默對望的時間如同凝結的冰,大家都不知所措。阿森精瘦,深邃的眼睛下有很重的黑眼圈,膚色偏黑;牙齒泛黑是長期抽菸的痕跡,尖尖的下巴,看上去很年輕。
電話響起後我一樣表明身分和來意,阿森還是顯得有些羞澀,講起中文來不如阿冀那麼流利。他告訴我,他現在在國中部的砂畫班,每天的工作就是畫畫,白天用砂,晚上則在房間用筆作畫。和他同班同宿舍的還有另外一個印尼人阿文,阿文之前請 TIWA 寄一些印尼風景的照片讓他作畫,阿森說若我寄自己的照片去,他可以為我畫一張素描像。
提到之前的案情,阿森看上去沒有阿冀那樣複雜的情緒,也許是個性使然。他平靜地告訴我,老闆常常罵人,他當時是年紀最小的,經驗不足不太會做,所以最常挨罵。「我不會看人,會害怕,會上火,當時工作才一個多月。」被罵得受不了,才和另外 2 人殺了老闆,然後想把船開回印尼,把漁獲拿去賣,最後被捕。20 的刑期,現在已經是第 9 年了。

圖/Yannis Papanastasopoulos@ unsplash
阿森的母親自他小時候就過世了,父親在 3 年前過世,曾有個哥哥在臺灣工作,似乎是做煮菜的工作,因不知自己患有糖尿病而在臺灣突然離世,現在家裡只有四姊。我問阿森從前在印尼做什麼,他說在印尼打魚、蓋房子,「我不是讀書的人,都用力量工作。」
在電話被掛斷之前,阿森要我和 TIWA 的大家問好。
阿森是那天的最後一個梯次,看完他出來,會客大廳已經沒什麼人了,辦理登記的窗口早已降下了鐵捲門,只有零星的家屬還在監獄的小賣部採買給家人朋友的物品。我走出接見大廳,時間還沒到 5 點,馬路上車輛往來,一切稀鬆平常。夕陽是夕陽的模樣,雲朵是雲朵的模樣。回望北監高樓,自由和刑囚,一牆之隔,不知道夕陽和雲朵,能不能飄進阿冀和阿森的窗戶?
這高牆之內,目前總共有 30 幾個印尼籍受刑人,被打散在不同的工廠工作。TIWA 認識並去探視的受刑人中就有 17 名是漁工,而其中 13 名都是境外漁工。雖然各自的案子不同,但皆是海上喋血案。

圖/Andrzej Kryszpiniuk@ unsplash
以「城外之人」之姿鑿刻境外受刑人圖像
海,是一望無際的,是美麗而廣闊的,被賦予無限生命、無限神話、無限詩意、無限憧憬。然而,境外漁工在離岸遠颺的那一刻,海,卻成了他們沒有高牆的牢籠。
不久後,我陸續收到阿森和阿冀的來信。阿森手繪了一張卡片,清真寺在紫紅色晚霞的映照下,發出寶藍色的聖潔之光,卡片正上方用螢光筆金燦燦地寫著印尼文的「開齋節快樂」。卡片內文滿溢阿森的感謝和祝福,還點綴著他畫上去的美麗圖騰。
阿冀則是自己用中文寫的信,字跡是小學生那樣一筆一劃的端正用力,他說目前在創作自己的作品,內容是來臺灣工作和在監獄的經歷和所見所聞。他在信末寫道:「只要還有一口呼吸在,就有無限的希望,就是最大的財富。」

圖/niu niu @ unsplash
此後我們便一直保持書信往來,有空閒的時間就會去北監探望他們。從每次短暫的 15 分鐘會面和書信往來裡,他們的情緒、性格和生命在我面前逐漸展開。有時我覺得自己是個拿著斧頭的竊賊,用力鑿開他們封存在記憶深處的苦難,拿著「城外之人」的自由權柄,野心勃勃地想要勾勒出一幅囚城之圖。
但我最終發現,自己的雙手,捧不起那分生命的重量,而我自己也深深陷入了囹圄之城。

延伸閱讀:
漁港都是人,與你我一樣不好不壞、時好時壞、又好又壞的人/《這裡沒有神》推薦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