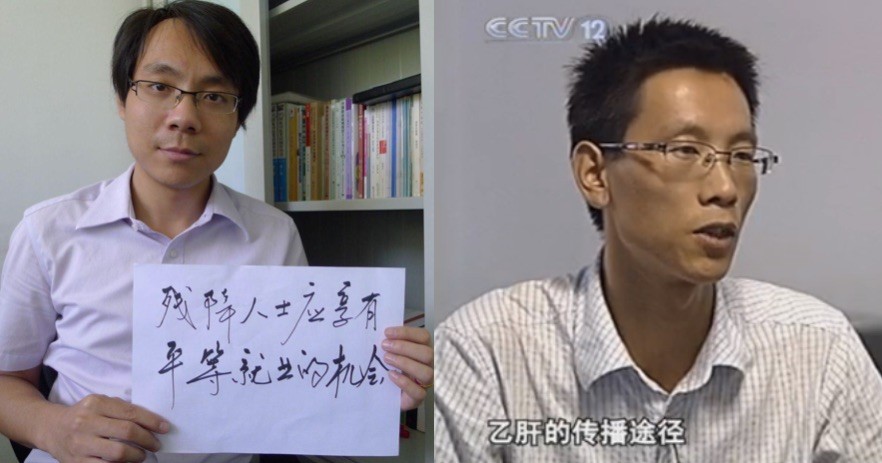為了愛情,還是為了簽證?難民營裡無可苛責的真實人性/NGO 工作者的日常囈語
在人道工作的領域裡,公與私究竟該如何畫分、在工作者與受照顧者之間究竟該拿捏著怎樣的距離,方能同理卻不流於浮濫,理性而不喪於漠然?

圖/Ryan Dam @ Unsplash
「所以他就這樣一走了之了?」我不可置信的問道。
丹尼爾嘲諷的撇了撇嘴,道:「這就是潔西卡來這難民營工作的第一年。愛上了一個未具文件的移民,陷入一段難捨難分的虛假感情,耗盡心力幫對方辦到難民簽證;最後他要的不過就是文件,而不是她的愛情。」
「然後呢?」我突然憐惜起潔西卡──我的頭頂上司,總是公事公辦、冷酷的難民營管理者。
「然後就是你看到的那樣。潔西卡搬出了難民營,刻意和每個人保持距離,不過問亦不參與移民們,甚至是志工們的私人生活,公私之間涇渭分明,只是每日按照著章程處理一切必須遞送的文件。」丹尼爾嘆息著。
4 年過去了,潔西卡如今才 28 歲,鏡片後的雙眼卻漠然得像是看透人世蒼涼。

圖/Paul Dufour @ Unsplash
公私難以涇渭分明的難民營
作為和這些未具文件的移民們一起在難民營生活的志工,我們天天一起洗衣、一起用餐、一起在烈陽下搬運贊助品、一起依循著難民營所規定的作息,我為他們上英文課、上瑜珈課、教孩子們寫字、與大夥兒共享生活中的喜悅及悲傷,不可免的會有情感的交流與參與。然而,作為短期志工,這兒只是我旅程中的一場經歷,但做為長期管理者,這卻是潔西卡數年來真實而沉重的生活。
「難民營裡的情感糾葛是見怪不怪的。」丹尼爾嘲諷的道:「在我們到達之前,我曾警告我的團隊們:難民營裡,一定會有移民找上你、誘惑你、試圖經營或是提供親密關係,這並不是因為你突然變帥、突然變美了,這只是對方在尋求某種利益與目的的條件交換,可能是保護與照拂、是資源、或是文件等,這是人性,沒什麼好怪罪的,它就是會發生。而這其中的不平等性會慢慢的以情感勒索的方式呈現,另一方面,人的情感是極為容易混淆的,尤其當你處於一個封閉環境之中,你的同情很輕易就可以被對方刻意加以利用,進而轉化為你個人認知上的愛情,而這樣建立在目的、同情與權力不平等上的畸形關係,自然注定以失敗告終。」

圖/作者提供
「但你總不能要求工作者或是志工與移民們保持距離吧!何況我們住在一起啊!日久生情總是難免的。」我質疑。畢竟,社會服務本身就是在於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我並不是要求工作者與移民們特別保持距離,而是要求每個工作者都清醒的理解到可能會發生的狀況與問題,並在心理上有所準備、不受動搖,尤其是感情方面,這很清楚的只是利益關係。基本上,在這兒工作,你每天必須要面臨的是生命的無奈與微渺、人性的殘忍及卑劣、人權的荒謬和虛偽等種種精神壓力,每個人或多或少一定會有情緒波動,你如果沒有做好心理準備,崩潰只是遲早的事。情感的投入、公私的距離這都是個人的事,你可以彈性調配,但我必須提醒你,在這兒,過多的情感投入,只會是無法承受的負荷。」丹尼爾頓了頓,不無唏噓的嘆道:「你也看到了,潔西卡的例子擺在那裡,你以為她沒有崩潰嗎?她的心裡已經空虛得什麼都沒有了。」

圖/作者提供
人道關懷往往出自於對人世的愛,然而,當你越是喜愛這份工作、越是投入,卻往往越是某種程度上對自我的傷害。我時常為這些移民友人們的經歷難過、為他們再次啟程後可能遭遇的事故擔憂,為他們始終堅守的微小的希望感到可愛而悲傷的傻氣,為一切的無能為力感到失落;這種種紛繁情緒往往在夜裡湧上喉口,卻巨大得無法宣洩,想表述些什麼,一張口開開合合卻只是不著邊際的空落,只得咽下,朝腸胃深處擠去,和白米、大豆、玉米餅和在一塊兒,化為肚皮下鼓脹的消化不良。
在難民營裡,個人的情感在盛大的悲苦和繁重的工作面前,渺小得不值一提;除了自我調適和做好情緒管理,我著實找不到其他的解決方法。公與私之間,怎麼可能完全分離?然而,個人的情緒、情感、甚至是善良,在這兒,卻往往也可能因人性而流於一種濫情與軟弱;總有那麼些移民們拿著自己的悲劇當噱頭、做消費,以換取更多的利益與資源。

圖/作者提供
始終活在過去的人道工作者
「這項工作很辛苦吧!每天要面對那麼多沉重的議題,你精神上一定不好受,可以告訴我,你是怎麼想的嗎?為什麼會願意投入這份工作呢?」拍攝中的紀錄片只剩這最後一段,潔西卡的訪問,我持著錄音機問道。
「確實是很辛苦,精神壓力也非一般工作可比擬,甚至這兒的生活環境與條件也極為艱困,然而,我認為必須有人站出來,為移民們努力,為人權發聲,為正義堅守立場,這是遠比金錢、舒適的生活、良好的物質條件更為重要的事;我既然已經看到他們殘酷的真實情況,我不能若無其事、更無法無動於衷。我對我正在做的事感到非常驕傲……」潔西卡口條清晰的回道,冰冷的、政治正確的言論。

圖/作者提供
我關下了錄音機。「我想,接下來這段我們就不錄音了吧!」
潔西卡疑惑的瞥了過來。
「我已經聽丹尼爾說了,關於 4 年前發生的事。你願意跟我談談嗎?為什麼,你還願意繼續這份工作呢?」風徐徐的拂過,她的表情從疑惑轉為簇著火光的震愕,我彷彿可以捕捉到潔西卡漏了一拍的呼息。
良久的沉默後,掩在鏡片下的雙眼只剩慘然的哀涼,她望向遠方,輕輕的開口:「有什麼好說的呢,這麼多年了,許多人來了又走。我留了下來,因為唯有如此,才能證明這不是虛枉,我們真的相愛過。每天看著這麼多跟他相似的人、相似的背景、相似的口音,看得久了,便彷彿他們都是同一個人,彷彿他一直都在這兒,但是啊,於我而言,最難堪的只怕是如何面對我對自己的懷疑。唯有繼續將這份工作進行下去,我才能說服自己,我的善意與動機,出自人權、出自對生命的信仰,對真理的堅持,而不是一樁滑稽的愛情。」她始終是活在過去的人,而他也仍舊是她的情緒出口。
延伸閱讀:
難民是社會問題還是受害者?被獵殺卻無聲,沒有臉孔而逃亡/NGO 工作者的日常囈語
陳岱嶺專欄/樂施會海地性侵案:除了敗德,NGO 駐外現場如何形塑性剝削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