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麼反社工師法?── 科大社工的 10 年尋思
我一直很喜歡《達悟族的精神失序:現代性、變遷與受苦的社會根源》裡所引用 C. Wright Mills 的一段話:
關於他們所忍受的煩惱,人們通常不會用歷史變遷和制度矛盾來解釋。關於人們的幸福,他們也不認為和社會的大起大落有什麼關係。人們很少意識到,個人的生活模式和世界歷史的軌跡有一種微妙的接合,一般人通常也不會知道,這種接合對於他們將變成哪一種人,以及他們可能參與、塑造的歷史有什麼意義。
如果,您問我為什麼反《社工師法》,我一定會回應您:我畢業於朝陽科技大學社會工作系,是個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後來,我就讀政治大學社會工作研究所。回顧這近 10 年的求學、工作歷程,透過這篇文本,我企圖將漂泊多年的身體和精神意識向讀者們交待和分享的是──我穿梭在歷史文本中所見的,還有跨越不同教育體制的同時所遇見的人事景物,如何讓我決意成為一名社工師法的反對者。

圖/Cole Keister @ Unsplash
社工師的立法起點:本是改善惡劣動盪的勞動條件
社工師的建制立法,一直被視為是臺灣社會工作社群邁向專業法制化的重大濫觴,但翻閱歷史文獻後,我卻也馬上就發現這是個天大的誤會。因為引發臺灣社工追求專業化的最初動機,最早其實是始自──政府部門約聘僱社工因自身勞動條件不佳所引起的納編爭議,而不完全是要建立成為一個專業的社群。
1970 年代,隨著旅美歸臺的學者和技術性官僚引介社會工作相關知識和發揮影響力,加上各地方政府陸續開辦各種實驗計畫(最具代表性的為 1974 年的小康計畫),以一年一聘的方式雇用社工員的成功經驗,使得美式社會工作專業的知識論述和工作方法,開始被本土行政部門吸納,亦使得社會工作就此得以在國家機器的邊陲取得一個較為明確的位置(鄭怡世,2007)。

圖/Ryan Tauss @ Unsplash
此後,隨著社會問題日益繁複,地方政府約聘僱社工員的人數逐年遞增,但一年一聘的不穩定性,加上長期同工不同酬與退休保障龐大落差,逐漸引發約聘僱社工員希望能夠納編為正式公務人員的勞動爭議,也逐漸激起社工界未獲政府重視和社會認可的危機意識。於是,以社會工作專業人員協會、醫務社會工作協會為首的「社工師法推動聯盟」,開始集結基層社工和學界推行社工師的建制立法。但因約聘僱社工員納編涉及國家考試制度無法順利成案,且考量納編訴求對就任於民間社福組織的社工人員並無實質助益,立法目標後來遂修正為「建立專業證照制度」,途中亦經過多個版本進行協商研擬,最終在 1997 年 3 月 11 日正式立法通過,並於同年 4 月 2 日公布施行。
所以,如果你要我說,我會說 4 月 2 日是大多數社工人開始被迫為奴的日子,而不是值得所有人同慶的社工日。因為,人們所熟知的歷史,其實早已被有計畫的掩蓋、扭曲及改寫。畢竟,4月2日真正的名稱是社工師日,從來都不是考不上證照的社工員日。
社工師法沒有說清楚的事:我們活在不一樣的世界
曾經,我和大多數的人一樣。懵懂追尋著昔日臺上師者的教誨,為了追上象徵專業的社工師證照,不假思索也義無反顧的投入為期 3 天(現在改成 2 天)的社工師考試,大概已是新世紀以來,社工人共同擁有的集體記憶。也不知曾幾何時,考題偏向學術取向,無法對應實務工作者的經驗,以及錄取率長年過低,開始變成社工人的夢魘。這雖然一度引起學界和實務界的衝突,但 20 年過去了,社工師法所引起的各種問題似乎依然無解。於是,考完時抱怨考題太難,放榜時抱怨率取率太低,似乎已經成為社工圈內某種無限輪迴的常態。
可是,在眾人關注考題和錄取率(或人數)的同時,我偶然有一個微小卻可佈的疑問和發現:「誰是社工師?」如同臺大駱明慶教授最知名的研究:「誰是臺大學生?」(參考:駱明慶(2016)誰是台大學生?(2001-2014)──多元入學的影響)特別是我某一天接連站在臺大、暨大、朝陽 3 間學校的社工系辦前,望著社工師的錄取人數,那一瞬間,真理彷彿就在眼前,頻頻對著我招手,但刺眼的真相卻令人不敢卒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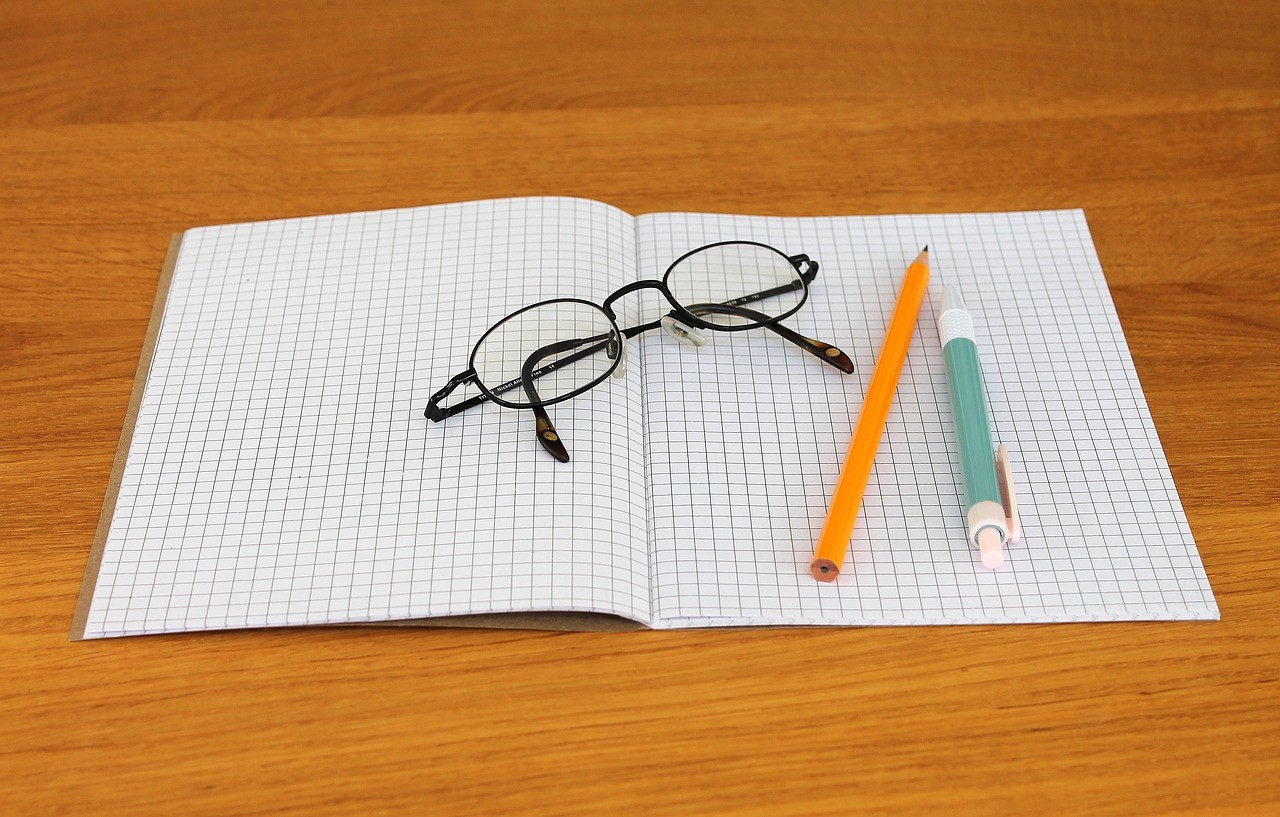
圖/Erbs55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引導社工師立法、修法的專家和學者,迄今從未提及,在社工師法所引起的諸多爭議中,特別是在討論錄取率或考題難易度時, 背後其實還有著一個更根本的問題──對比著文化資本較為厚實,畢業於好學校,可以 1、2 次就考上社工師,接著得以較順利考取公職社工師的前段社工學院的學子們,人們很少認真看見許多就讀中、後段學院的社工夥伴裡的生命有一種殘酷,特別是原本家庭經濟條件可能較差的他們,畢業後往往背負著學貸,再加上始終無緣考取社工師,更有許多人就此被迫任職於勞動條件較差的社福單位,只能苦苦等待翻身的機會。甚至,這些人很多時候還會被前段社工學院的教授們指責是他們自己不努力、程度不好。
類似的無奈,相同的問題,在我畢業回到南部工作、兼課後,依然反覆出現在我的眼前。對此,我始終相信這已無關乎個人努不努力,更已超脫乎個人聰明才智,而是一種社會的不平等。至於這個不平等的現象,社會學的訓練告訴我,它叫做「階級複製」;社工的專業養成告訴我,要與其為敵。因此,我必須指出社工師法製造的撕裂,始終不只有社工師和社工員的階級對立,而是一路從家庭出生、學校機構,透過證照再次強化運作的階級再生產。這也才是社工師法真正問題之所在。
我始終認為從來沒有人不努力活著,不管是學分班社工、科大社工或高教社工皆然。但在社工師法的制度下,我們的處境確實就是不一樣。如何認清彼此的差異和不平等,或許是某些社工人生歷程必然被迫要面臨和處理的功課,也或許某些社工終其一生不須思考和面對這些衝突。這是我這幾年走了 10 幾間學校的發現。
為此,我總是在想,難道我們真的不該問問自己,即使活在不同的世界,但同樣作為社工,我們難道不能有稍微平等一點的機會嗎?至少,我們應該彼此看見,不是嗎?

圖/Bethany Legg @ Unsplash
從專業主義轉向民族主義:超克社工師法的想像共同體
通常而言,社工師法使得臺灣社會工作得以自視為是一門專業的認識起點,主要奠基於 Greenwood(1957)對於專業的 5 項基本特質之理論基礎。此外,社工師法雖然讓臺灣的社會工作開始得以成為一門具有獨立且具有排他性的專門職業,我們卻也可以看到,自1997年社工師立法起,臺灣的社會工作社群一路排除了傳統宮廟的助人者、山地原住民社工、非社工本科系的社工;10年後,也就是2007 年(96)第 2 次社工師修法,我們更可以看到社工師考試資格調整了必要科目和學分(從 20 學分改制為 45 學分),這除了影響各學院的教育安排,原先 20 學分班的成員也從 2016 年底新法施行後,開始面臨可能的被排除危機。然而,也就是在這裡,我意外發現有一個極其矛盾的歷史斷點,那就是所謂的科大社工。
科大社工,技職體系社會工作系的科大社工,不同於傳統普通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的高教社工。縱使許多人總是說,畢業了,工作了,在專業程度的表現上,2 者根本上沒有任何差異。我原則上同意這件事情,但我還是必須說,科大社工和高教社工不一樣,因為技職體系科大社工迄今仍不斷承擔著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歷史汙名,使得技職體系的科大社工,被迫成為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歷史的他者。

圖/IvanPais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或許您會問,什麼是偏見,什麼是歧視,或什麼是他者?例如,臺大社工教授林萬億,就曾以「特例」形容技職體系最早設立社工學程的屏東技術學院(後升格為屏東科技大學)應用生活科技系(1996 年),或者亦曾透過研究試圖證明技職體系社會工作系的專業師資比較有問題,進而指出學生的專業養成恐有疑慮,甚至我也不只一次在公開場合聽聞臺大、政大名師對於技職體系社會工作系師生的口誅筆伐。
可是,這些教授絕口不提前段社工學院對於中、後段技職體系內專業師資的磁吸效應。難道,這不是偏見?不是歧視?您真的可以非常有自信的說出:科大社工真的毫無疑問是臺灣社工社群的一份子,而不是社群的他者嗎?
但也就是在這裡,我發現我們可以透過專業主義來解釋社群如何一路排除傳統宮廟的助人者、山地原住民社工、非社工本科系的社工,乃至 20 學分的學分班社工。可是,專業主義卻始終無法明確回應──為什麼同屬社群內的技職體系社會工作系的師生會被特別標籤,甚至受到歧視,最終成為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歷史的他者?而此種在社群內部不斷的標籤、分裂、排除,但卻又要讓被標籤、分裂、排除的受壓迫者自視為同一群體的操作過程,其實是很「民族主義」(Nationalism)的。

圖/latko Vickovic @ flickr, CC BY-NC-ND 2.0
所以,我們探討社工師法不應只是關注專業社會學對於「專業」的定義,或是文化資本優劣所引發的考照爭議,而應更進一步涉入類似民族主義的「認同」衝突。如果不這麼做,諸如科大社工或學分班的社群成員,或許永遠只能是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的他者。換言之,我認為社工師法對於社工群體帶來的衝擊和影響,不僅只是不斷對於社工社群內部進行分類,然後排除某部分邊緣缺乏機會發聲的人們,還有更可怕的其實是──社工師法作為一種統合不同身分類別社工人的想像工具,它讓所有的社工人有了一個認為自己是社工的專業認同標準,想像不同的彼此成為某種共同體。
不過,這個由社工師法所製造的專業認同標準其實是虛幻、浮動又不斷變化,而且是受社群菁英操弄的,更持續透過教育系統在日常生活中傳播的。這使得社群菁英得以讓他們對於社群內少數群體的偏見和歧視行為被合理化和正常化,然後堂而皇之的以不符專業之名,理所當然的驅逐他們。
如若我們一起認真回頭反省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發展的歷史,難道不是上述如此嗎?而這真的是我們當初期待的社工師法?我們所追求的社會工作專業嗎?

圖/Jamie Street @ Unsplash
因社工師法而生的利益團體
不知是否還有人記得,當初一群專家學者號召人們上街頭爭取社工師立法時,曾經表示社工師法將帶給社工人一個有個美好未來的許諾。但 20 年過去了,敢問社工師法除了給予社工人一面「專業」的神主牌和不滿的情緒之外,究竟還留下了什麼呢?事實上,社工師法的美好許諾迄今不但沒有實現,反而還留下了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
我們可以看到,因著社工師法的規定,執業者必須強制進行職登。為此,各縣市開始設立所謂的「社工師公會」,後來於 2002 年數個社工師公會正式集結成立社工師全國聯合會,社工師的公會組織制度開始全面啟動。然而,放眼這幾年,許許多多有關於社工權益受損的事件,我想問的是──當基層社工遇到勞資爭議時,特別是對於許多社福組織薪資給付不足(回捐),明顯違反行政倫理和偽造文書的爭議事件,乃至被惡意解聘時,社工師公會或全聯會,願意主動介入協助嗎?或者,公會儼然逐漸成為政府部門和社福組織主管/雇主及專家學者們(因為他們比較有時間)的禁臠之地,只是單純的收取規費和舉辦繼續教育學分認證課程圖利少數人,根本沒有實際改善基層社工惡劣的勞動處境?

圖/Caitlin Oriel @ Unsplash
如果,因社工師法而生的社工師公會,不能與基層社工站在一起,回應基層社工的需求,那社工師公會為何能持續收取會費?又全聯會怎麼可以代表所有沒有社工師證照的社工員?說得更白一些,因著社工師所成立的這些專業組織,不但有著社群代表性的疑慮,而被少數專家、學者及雇主輪流寡占的經營狀態,同時還有剝奪所有基層社工得以團結發聲的可能性和機會之疑慮。對此,我想再問您一次,這樣的社工師法,您真的還要繼續支持嗎?
社工師法的存與廢:是反霸權?還是廢社工師法?
親身見聞許多事件,在歷史的文本中反覆找路許久,反社工師法對現在的我而言,已經沒有太大的內心掙扎和懸念,但某個掛在心頭許久的疑惑,前陣子偶然看到一位師長在臉書的提問後開始被放大(就好像是逼著我要面對考上社工師卻反社工師的自我矛盾)。我理解這位老師的問題大概是:反社工師法,是反因社工師法而生的霸權?還是反對社工師制度,所以要廢除社工師法?
社工師法已經 20 年了,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嚴肅卻又急迫必須要正式面對的提問,對於這個問題,我確實也有某種特定但又有點搖擺未定的立場,但我也很好奇,反社工師法的大家是怎麼想的呢?所以,我有個放了很多年的想法想要去做──我想要辦一個反社工師法的論壇。

圖/作者提供
初步的想法大概是,我想要找一個大空間,花上一整天的時間,然後需要一筆錢(大概 5 萬元),邀當初上街頭爭取社工師法、後來卻罵狗屁的李雲裳,當初的漂流社工群和陶蕃瀛老師,讓社工師錄取率變成 44% 的王增勇,還有 80 後世代反社工師法和投入組織工會的夥伴們。我很想要透過論壇重新把反社工師法、對於社工師法有疑慮的大家重新串在一起,討論我們的下一步,忠實的記錄下來,然後再傳給下一個世代,不然現在好像越來越少社工在意這些事情,更不知道前面的社工經驗過什麼和做過什麼了。
這件事情或許會花點時間,但如果您也不甘持續作為社工師法的奴隸,覺得想一起行動,想要重新追尋作為社工的自由和尊嚴及不一樣的真實在地歷史,麻煩你就留言給我吧。
就從這裡重新開始,我們一起想辦法反社工師法吧。
參考資料:
鄭怡世( 2007 )。〈台灣社會工作發展的歷史分析:1949-1963 年「社會部所從事的工作」與「美式專業社會工作」雙元化的社會工作認識〉,《社會政策與社會工作學刊》,第 11 卷第 1 期,頁 153-197。
延伸閱讀:
打開社工師法的潘朵拉之盒:不合時宜的社工師法,如何分化社工群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