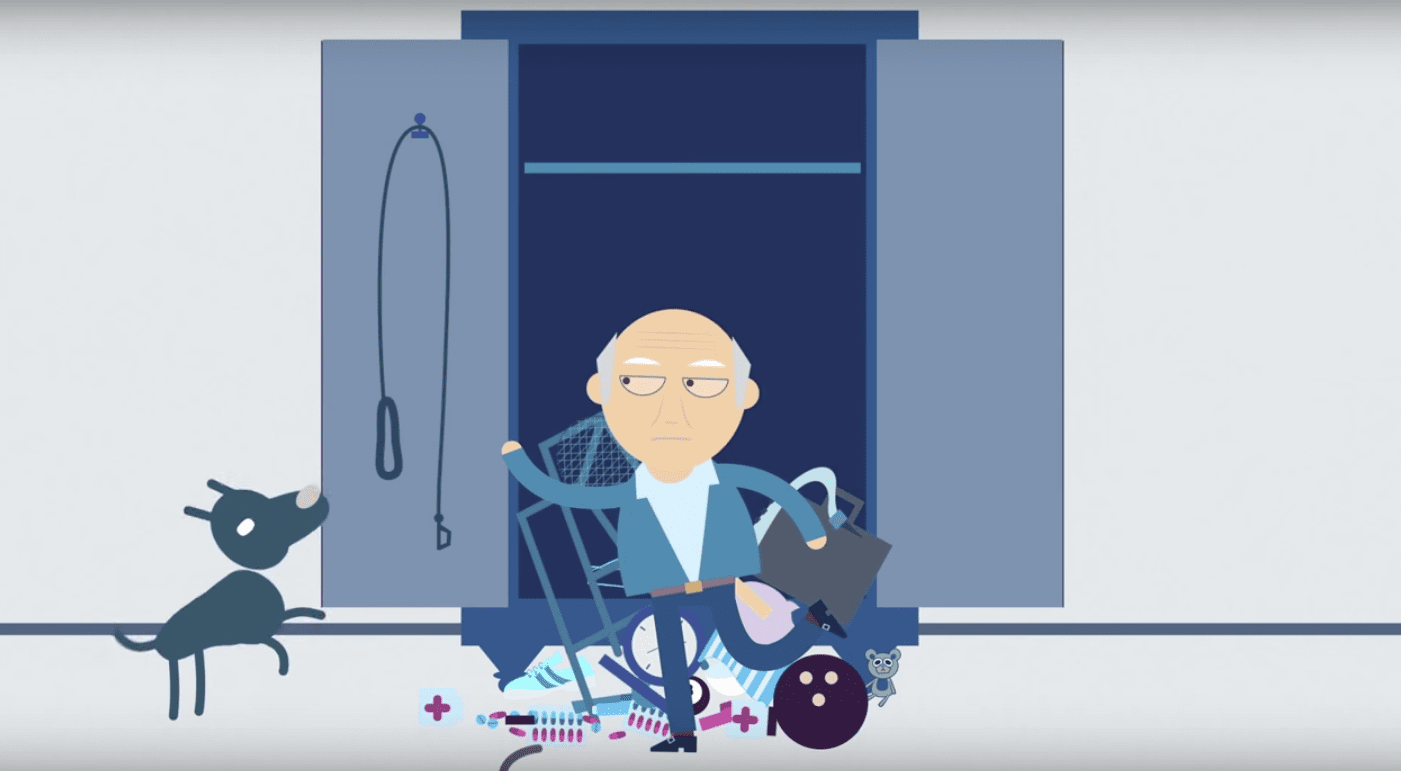人權是一句髒話?「強制住院」是精障家屬的救贖還是患者的權利傷害?(上)
編按:
從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CRPD)在國際審查後,委員於結論性意見明確提到「強制住院」違反公約;到今(2018)年 1 月 3 日,收容逾 500 名精障者的龍發堂因為去年底陸續爆發阿米巴痢疾、結核病等群聚感染而宣布解散,將暫停精障照顧,引發精神疾病者、家屬、工作者之間極大的爭論。
法國當代哲學家與社會學家米歇爾‧傅柯(Michel Foucault)於其著作《瘋癲與文明》中提到,中古世紀蔓延著痲瘋病的歐洲,有人為了擺脫異己,便將痲瘋病人擱置船上,令其漂流他方,當時這些船隻被稱作「愚人船」,這樣的「隔離」與「放逐」意味著強調理性的社會對「異己」的想像是危險、骯髒,或不理性、瘋癲的。
飄蕩了幾百年的「愚人船」,如今靠岸了嗎?
本篇將由現代精神醫療中的「強制住院」談起,說明強制住院的能與不能。面對精神障礙者,好似第一個想法就是服藥,如果不願服藥或是服藥未見改善,那就只好隔離,讓他和身邊的人能夠「保持安全」,社會默認了這似乎是沒辦法的「必要之惡」。然而,對於那些在和精神症狀掙扎的當事人、已經撐不下去的家庭來說,這會是唯一解方嗎?
文/郭可盼、鄭珮琦 伊甸基金會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註 1)
在精障者急性發病、有自傷或傷人的行為時,強制住院常常是精神障礙者家庭裡的最後一道防線,協助不願意自願就醫的案主藉由這個過程可以住進醫院,確保自己與他人的安全並且接受醫療的協助。
然而,今年在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CRPD)國際審查後,審察委員明確提出強制住院違反公約第 14 條「禁止基於身心障礙的因素,或是非法、任意剝奪身心障礙者的人身自由。」的結論性意見。委員表示,每個人不應該因為自己的障礙,在沒有經過法律的判決下被限制人身自由。聯合國 2006 年的「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揭示保障身心障礙者人權的規定,具有國內法律效力。桃園地院孫健智法官依照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施行法規定,在 106 衛 4 民事裁定停止一位精神病患的強制住院。然而,這個結論性意見和後續孫法官的判決出來,許多在醫院、NGO 和精神障礙者實際工作的一線工作者和家屬卻罵翻了。
有醫生投書表示:「強制住院」雖表面上看是剝奪病人自由選擇的權力,實際上是為了保障病人接受精神醫療的權益。孫法官打著保障人權之名,反而剝奪了病患在接受治療後病情改善的機會;再者,如果無法將危險性高的患者隔離,造成社會問題,再經媒體渲染,恐讓民眾更為排斥,回歸社區將更遙遙無期。
但也有人投書,指出現行強制住院的缺失:精神科醫生可能會在社會氛圍及輿論壓力下,為了安全考量,往往傾向限制病患自由、在決定是否要強制住院時,能給病患實際陳述之機會仍有不足、缺乏物證等原因,讓強制住院的過程中可能有瑕疵,傷害到精障者的人權。

圖/ Designed by Freepik
身為一個和照顧者一起工作的社工,我想起那些雖然家人被精神症狀嚴重困擾,但是在家中還找不到施力點的家屬,常常強制住院的過程讓他們非常痛苦,但是似乎成為現實狀況中的最後一個選項。
強制住院好像變成了家屬和精神障礙者 2 者的權力拉扯,成為顧全精障者自主性和使之得到醫療照顧的 2 難決擇。在那一刻我沒有說話,虛無飄渺的人權似乎只像是一句髒話,讓被期待要對病人負責,或是希望家庭得到協助的家屬毫無施力點,對於現況一籌莫展。
什麼是「強制住院」?
精神衛生法 41 條:「嚴重病人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經專科醫師診斷有全日住院治療之必要者,其保護人應協助嚴重病人,前往精神醫療機構辦理住院。」
由上所述,強制住院的啟動要件有 2,一是強制住院的對象為嚴重病人,嚴重病人的定義是指「病人呈現出與現實脫節之怪異思想及奇特行為,致不能處理自己事務,經專科醫師診斷認定者」;二是自傷傷人,表示該位當事人自我傷害或傷害他人時。

圖/Vladislav Muslakov @ Unsplash
當精神病人送到醫院後,經過 2 位精神科醫生強制鑑定為屬於嚴重病人,精神病人本人不同意住院或無法表達時,檢附嚴重病人及其保護人之意見及相關診斷證明文件,向審查會申請許可強制住院,經過由專科醫師、護理師、職能治療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及其他相關專業人士所組成的、7 人以上的審查會同意後,才可以強制該病人住院。
一個精神病人被強制住院,不得逾 60 日,但經專科醫師鑑定若有延長之必要,並報經審查會許可者,得延長之,每次以 60 日為限。
CRPD 與強制住院的衝突
既然強制住院是在危急的情況下,將不能控制自己精神狀態與行為的人送醫,那這聽起來很合理啊,為什麼國際審查委員認為這有侵害人權的問題呢?
第一,「強制」代表了這個醫療安置不是病人本人的自主決定。一般的民眾,在我們生病的時刻,我們可能會因為手邊有工作要完成而決定週末再去就診;或是我們會選擇自己信任的醫院和醫師;即使身體不舒服,我們也有不接受醫療的權利;然而對於精神障礙者而言,「強制」意味著以上一般人的自主選擇權都沒有。機構中曾有精障者表示,因為自己生病,和家人有衝突時,理所當然被認為是「發病」、「有問題」的一方,會擔心家人「把他強制住院」。因此,「強制」是對於身心障礙者「自主權」與「法律能力」的侵害。

圖/David Cohen @ Unsplash
其次,當一個精神障礙者經由強制住院後,認為自己的遭遇不公想要提出司法救濟,他們通常無法和其他人一樣走上程序保障較為完善的司法管道。舉例來說,如果一個人對於被強制住院的決定不滿,希望提起行政救濟、想要聯繫律師時,因為大部分精神科病房都禁止使用手機,只能使用公共電話,連繫上很不方便,律師也沒有辦法主動打電話給他。因此,強制住院在遭受限制人身自由的程序中,沒有獲得「平等的司法保護」。
最後,當人身自由受到限制之時,更容易遭到「不當對待」。強制住院讓一個沒有意識到自己有疾病的精神障礙者可以得到醫療的幫助,進而有穩定下來的可能。但這是一體兩面,當一個精障者覺得自己所遭遇的醫療對待是不正確的,在強制住院的情境下他相對沒有拒絕的權力。對於一般去醫院門診的病人和家屬,當與醫生互動時,不管是覺得和醫生溝通不良、互動困難(例如病人覺得現在的藥物副作用很大,想要換藥,但醫生不願意與之溝通和討論),都有可以轉換醫生的權利和自由,但是在強制住院的過程中,精神疾病患者不能轉換住院醫生,如果遇到很不適合的醫生或遭遇不當對待時,相較於一般人,會更容易遭受不當對待。(參考:【CRPD 星期天|人約盟說書:第 12 回】人身自由與安全篇)

圖/Katherine Chase @ Unsplash
強制住院幫得上的忙
住院對我而言最有幫助的是隔離外界資訊。由於病房(尤其急性病房)是極為隔離性的環境,因此能隔絕外部壓力源的刺激,讓人心神平靜。比如有一次我在大廳閒晃時,不小心聽到那陣子特別刺激我的新聞,我霎時情緒崩潰,一邊哭一邊發抖著請保全轉臺;如果我是在醫院外,可能會更常經歷這個情境,這對當時的我而言是不堪承受的。(摘自〈我該去精神病房嗎?〉)
1. 家屬和當事人的緩衝空間,可以重新調整腳步
會啟動強制住院,常常不只是由於當下的單一事件,而是代表此家庭已經像燜燒鍋承受了長期的壓力,當下的事件僅是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因此,強制住院期間能讓家屬稍稍喘息,精障者也能暫時隔絕原本的壓力源,使雙方都得到一個緩衝的空間。
對於精障者而言,住院是在一個刺激較少的空間與制式化的時間安排下,有機會可以好好休息、把自己穩定下來。對於家屬而言,藉由精障者住院的空檔,也可以重新調整腳步,藉機學習,調整與生病的家人相處的方式以及思考接下來該怎麼協助他。
2. 精障者得以取得醫療資源
根據斯德哥爾摩所做的一項統計,一個人從開始生病到實際進入醫療系統,所需的平均時間是 1 至 3 年(Seikkula 等人,2001);而實務工作中,我們也常看到很多家屬已經察覺家人有異,例如覺得有人跟蹤、家裡被裝監視器、聽見聲音等。雖然對於別人來說,這些都是幻聽、幻覺,但對當事人來說卻是非常真實的感受。因此家屬往往很著急地希望生病的家人可以就醫,但患者若覺得自己沒有生病,不願就醫,也就無法啟動後續的醫療、心理、社福相關資源。
藉由住院過程中的強制服藥,當事者的幻覺有可能不再繼續出現或讓情緒穩定下來,如果配合身邊工作者和醫生的討論,也可能藉由這個歷程理解到自己需要協助,願意開始服藥、回診,並且讓其他的資源進來協助。
3. 經由住院期間密切觀察,調整適合的藥物
精神科藥物在不同的人身上會產生相異的效果,例如有人吃了某藥會變胖,另一人吃了相同的藥後反而變瘦。因此,精神科藥物的調整是一個不斷試誤的過程,必須調整到可以穩定精障者的症狀、觀察服藥後的副作用等。
平常若在門診,最多只能 1 週追蹤 1 次,而且高度依賴精障者或家人的口述來調整藥物。但是在住院期間則會密集監測精障者的狀態,以相較於門診更快的速度和更完整的資訊,調整適合當事人的藥物,減少過程中因藥物副作用而造成的折磨。
強制住院幫不上的忙
住院對我而言最大的幫助是隔絕外界的刺激,但事實上,我認為它最無法幫助我、甚至最大的弊害也在於此。住院隔絕了所有的刺激,不分好與壞,而這些所有好的與壞的刺激共同構成了生活的實感。因此,隔離的環境也能把人逼的焦慮不堪,我自己到住院後期時尤其會如此,因為缺乏日常生活中和他人的平凡互動(如出門買東西和店員互動、與朋友閒聊、走在街上看人群來去等),我變得坐立難安,無法感受到時間的流逝,以及從和他人的互動中形塑而成的自我,遂度秒如年。「隔離的病房是無法讓人回歸社會的」,這是我出院當天行走於川流的馬路時,心中反覆迴響的一句話。(摘自〈我該去精神病房嗎?〉)
1. 患者與照顧者出現更大的衝突
強制住院的過程中,由於違反精障者本人的意願,可能會滋長其對家屬的怨懟,覺得是家人把自己「關起來」,造成家庭更大的分裂,這將使出院之後的相處更加緊張,反而有害照護。
當精障者覺得自己是被關起來時,這樣的衝突未必能讓他意識到「我需要幫助」,反而會認為自己是被家人逼或騙到住院,因此離開醫院後,不願意繼續回診服藥和接受協助。

圖/Noah Silliman @ Unsplash
2. 單單藥物協助並不足夠
住院僅能在個人層次提供藥物治療,但藥物只能解決生理的問題,而生病往往是由於心理和社會因素,但這些因素如家庭原先面對的照護困境乃至社區對精障者因不解而生的恐懼,都無法獲得相關資源或協助。因此,在出院之後,精障者、家屬及社區面對的困境依舊存在。
現行的制度讓住院只以醫療為重的原因很多。以健保給付為例,心理治療和社福的給付點數太低,使醫院缺乏聘用足夠人力的動機,在急性病房的生活安排中,順位也比較後面。曾有精障者表示,她吃了 15 年的精神科藥物並有多次住院經驗,但只接受過 2 次心理諮商。此外,因為健保點數的影響,職能治療師沒有辦法量身訂做那些協助住院的精障者回歸生活的準備和復健,反而針對許多異質的病人設計團體課程,因為同樣 1 個小時,職能治療師帶團體可以申請數 10 名病人的健保點數,而量身訂做不符成本。然而這也造成病人無法獲得個人貼身實用的細緻服務,以致於復健效果大打折扣。
由於急性病房成員的異質性很高,如何設計團體活動也是一門學問。為了讓大家皆能參與,也由於醫院事務繁忙,團體活動通常都非常簡單,這讓所謂「高功能」的病友往往無法忍受。比如我之前曾認識一位高學歷病友,其診斷是躁鬱症,她對於摺紙、畫圖、看電影等活動興趣缺缺,卻要壓抑而不能表達意見,因為一旦表達不滿和不耐,就會被認為是躁症發作。帶領急性和日間病房的職治師也曾無奈表示,由於急性病房的組成較日間病房更為多元,很難同時滿足大家的需求。然而,無論有多少活動可以選擇,病人仍只是被動被提供選項,而無法針對個人的需求量身訂做其最需要的。(摘自〈我該去精神病房嗎?〉)

圖/Yoann Boyer @ Unsplash
3. 出院後與社區的轉銜機制流於形式
最後,精神科病房封閉的特質,使其成為「真空」的環境──如同前段所述,它僅能暫時隔絕精障者與家屬和社區的緊張關係,因此從醫院到社區的轉銜就變得相當重要。目前醫院為此僅能做到的是「出院準備服務」──擔任精障者與家屬的溝通協調者,或者轉介相關資源,而不是回到家庭與社區生活的準備。然而,由於健保與以往對此的給付相當低(註 2)、社區資源稀少、醫院與社區缺乏連結平臺,因此出院準備服務還是以醫療觀點來看待出院的準備,而非以家庭與社區生活如何支持患者為需求核心,以上因素皆讓出院準備服務流於形式。
沒有好的銜接,讓精神科急性病房成為旋轉門。部分精神障礙者即使在強制住院後穩定下來,回到社區後卻復發,然後再住進去。況且,仍有部分病患不會因為強制住院而有病識感,反作用是出院後更不願意接受治療,因為強制住院的過程帶來的是身為精神病患的恥辱感與汙名,使他們對於精神疾病的認同度更為降低。患者往往並非認為自己不需要協助,但不想遭受被作為精神病人的不當對待與歧視。
接下篇:當精障者與家庭都累了,難道我們只剩下「強制住院」這個選擇?(下)
註解:
1. 伊甸基金會精神疾病照顧者專線 02-2230-8830。以家人陪伴家人,由照顧者接聽照顧者的專線,或搜尋臉書:瘋靡 popularcrazy
2. 「出院準備服務」之健保給付已於 2016 年提升為 1500 元,但距今只 1 年多,還未能看見具體成效。
參考資料: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