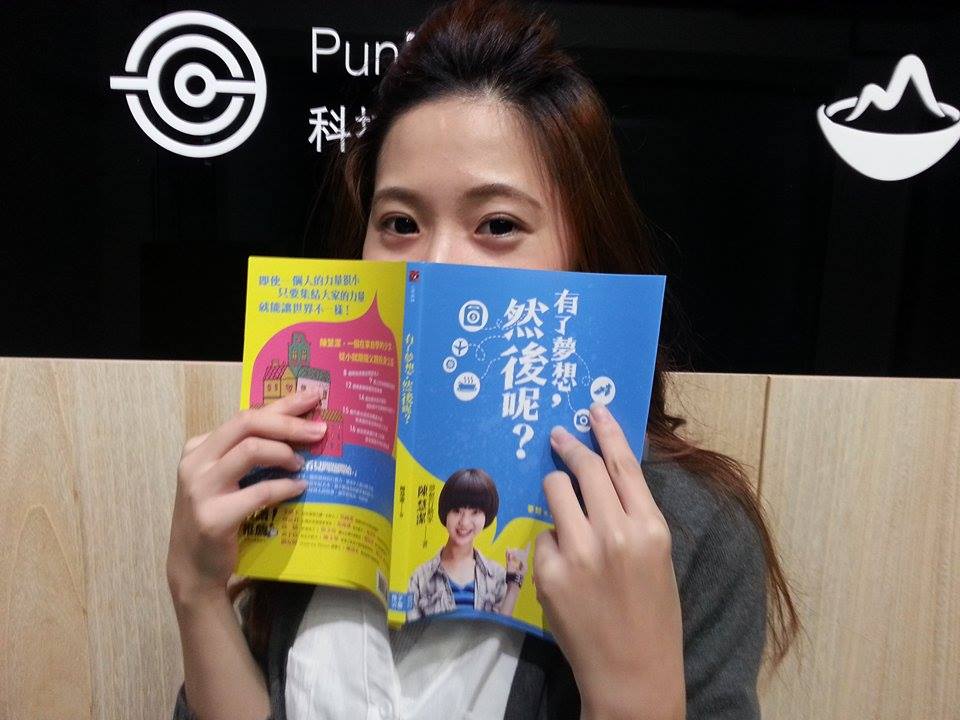肯納,信任和勇氣打造出來的夢想村莊! /《孩子,我要和你一起老去:打造愛與夢想的肯納莊園》推薦序(王浩威)
編按
心靈工坊今年6月出版《孩子,我要和你一起老去:打造愛與夢想的肯納莊園》,關懷肯納症者(低功能自閉症者)與照顧者的困難現況,並記錄台灣首創的雙老家園模式。二十年的時間,從花蓮肯納園到龍潭肯納園,一點一滴的替肯納症者開拓生活的空間,讓他們同樣也擁有幸福生活的權利。NPOst獨家完整刊載由知名作家、精神科醫師王浩威撰寫的推薦序文,引領讀者探見雙老家園,並思考肯納症服務的創新服務模式。
文/王浩威(精神科醫師、作家)
我自己雖然擁有兒童精神科專科醫師的執照,算是臺灣第一批本土訓練出來的兒童精神科專科醫師之一,也就是一九八○年或八一年左右,宋維村教授開始主持的兒童精神醫學次專科培訓的成員之一;卻沒有像同一期的成員,包括吳佑佑、張學岺、林亮吟、王怡靜、王雅琴等等,一直堅守在兒童精神醫學的領域。
一九八○年到一九八四年我在花蓮的某個醫學中心工作,當時東臺灣(臺東、花蓮、還有雪隧還沒打通以前的宜蘭)好像只有八、九個精神科醫師。而接受過(不完整的)兒童精神醫學訓練的,除了在羅東的王怡靜,好像就只有我了。也因為如此,當時全國兒童身心障礙普查也好,兒童福利法通過以後相關的問題處理也好,或者是省政府中學輔導網絡,只要是與兒童或青少年有關的,我都要硬著頭皮上陣。也是因為如此,我的老師宋維村教授才要我每個禮拜回臺北接受有系統的訓練。
當時雖然參與了這些兒童心理的相關工作,在門診也有兒童青少年心理專門門診,也負責東部地區初步篩檢普查出來的疑似自閉症兒童(其中有很多只是選擇性緘默症),但真正自閉症相關的診斷和處理,其實是相當少的。也因為如此,後來能夠和肯納基金會結下這麼深遠的緣分,其實回想起來是相當不可思議的。
我自己離開花蓮以後,二○○三年,肯納園在花蓮壽豐鄉成立了,這是四個肯納家庭、臺大醫院兒心中心資深治療師詹和悅,以及退休的楊思根教授,一起開始的一個夢幻般的計劃。詹老師是我在臺大兒心日間留院受訓時的老師之一,而我在臺北因緣際會所認識幾個肯納家長,則包括李幼珍女士介紹的彭玉燕董事長。當時,因為花蓮還有很多繼續合作的夥伴和社區工作,我也就經常回去花蓮,自然就會去壽豐的肯納園走一走,也因此和他們一直保持著聯絡,包括陪伴當時在密西根大學還沒退休的蔡逸周教授夫婦,一起去參觀等等。在這個過程裡,陸陸續續地,也開始聽到許多完全沒辦法事先預料到的困難。

看見肯納困境
現在回想起來,花蓮肯納園等於是一次先期的嘗試性實驗。當時,我也逐漸進入中年,成為一位稍微有經驗的精神科醫師,也就越來越感覺到許多身心障礙孩子的問題,根本不是幾位厲害的專業人員或一間傑出的機構就可以解決的。同樣的,有著完全願意付出的父母或家庭,甚至就算富可敵國的家庭,還是沒辦法解決自閉症孩子的所有問題,包括從小時候的成長到一般人年長後的善終。
這時候,因為一直在一起的緣故,也開始和肯納園或肯納基金會先期的家長們,開始去研究和參觀其他先進國家是如何面對肯納孩子長大離開學校以後的許多問題。我們很驚訝地發現,在日本並沒有這樣的民間組織,更沒有官方有系統的資源提供;我們也發現,在美國這樣的組織是以民間為主,然而真正能夠將成功的模式維持一定持續性的,而且真正尊重這些肯納人基本的尊嚴,其實是找不到的。至於在北歐或荷蘭、比利時等地方,也許有一些還不錯的例子,但是他們的肯納人是十八歲以後就完全由國家來負責,並沒有像臺灣這樣,父母不能分離也不可以分離的情形,所以處理起來就完全不一樣了。
在亞洲的國家裡,親情是一輩子的關係,這不只是產生了不同的文化面貌,也影響了不同的精神病理所形塑出來的樣貌。當然,這也就是為什麼許多西方的福利制度,搬到了包括臺灣在內的亞洲國家,往往都變得窒礙難行。
在觀察花蓮肯納園的經驗裡,以及跟這些家長的相處的過程中,我慢慢有了三個想法:首先,病人不是只有病,還有更長遠也更普及的「人」的問題,而專家只有在面對「病」的時候才是專家,最基本的人的生活卻往往都沒有看到;其次,所謂身心障礙這樣的生命的特殊困境,往往不是幾個專家或父母自己就可以支持一輩子的,而是需要一個村,需要建立起一整座的村莊,才能夠真正有機會完成的;第三,雖然有了可能成功的計劃,但對於完全創新的新途徑,特別是在這個地球上每一個國家都沒有看到的嶄新方式,是很難去說服臺灣這個島嶼上沒有同樣貼身經驗的人們,不論是熱心社會公益的中產階級或有錢人,還是永遠設想不夠周到而創意也比不上同心協力的家長的國家機器。只有真正去做,只有在錯誤中慢慢摸索前進,讓想法變成了具體而看得見的模樣,別人才有可能相信。因此找到可以解決問題的夢想計劃是要靠自己的雙手和血汗慢慢去完成、沒有其他的人會幫你打造的。

一座村莊一起來努力 打造肯納雙老家園
所以,當彭玉燕女士詢問我的意見的時候,我對這種近乎建村的雙老家園概念,當然是舉雙手贊成的。「所有的孩子都是整個村莊一起撫養長大的」(It takes a village.),這是希拉蕊還是柯林頓總統夫人時常常提的話(也用這個當書名寫的一本書),據說是來自非州某些不同部落的諺語;同樣的,在面對現代社會許多新的問題時,往往也是要 takes a village(有一座村莊一起來努力)。譬如臺灣目前面臨年齡老化的社會,共老家園或共老社區的提出,就一樣是「一座村莊一起來努力」的理念。而,如果連中產階級的養老,都必須要打造一整個村莊了,就更不用提這些肯納家庭了。
肯納雙老家園的宗旨也是這樣,當肯納兒的父母逐漸老去,這樣的養老村是需要大量人力的;在這個家園裡,不容易被社會接受的肯納兒,有了勞動的機會,有了因為勞動成就而有尊嚴的機會。除了養老村,還有各種作業所和社區住家中心。自閉症或肯納症的其中一個特色就是固著性。肯納兒的生命,他們的情緒,他們的心理,他們的生活狀態,是和整個環境百分之百結合成為一體的。然而,一個環境的熟悉感一旦被破壞了或改變了,整個人也就失去了原來的穩定情緒。如果肯納兒在父母的陪同下,逐漸熟悉的這個村莊,逐漸成為村莊一起工作的一員,也會逐漸習慣住在單人的住家中心;這時候,如果有一天父母往生了,他還是有一個他所熟悉的村莊以及一群互相熟悉的村民,這樣的環境也許可以穩定住失去了父母的他,包括他的生命和他的情緒,自然也就可以穩定了他的心理健康,而不至於整個人又要因為環境的改變而崩潰,然後被送到慢性療養院,從此再也出不來了。
同樣的,當肯納兒的父母走了以後,這個家可以轉手給下一個肯納家庭,讓年齡適當而必須做同樣安排的肯納家庭也有加入的機會,同時這筆轉讓的經費就可以成為肯納兒以後生活的信託基金,這也讓不得不先到天上的父母,臨終前不用再有任何擔心。

當夢想碰撞現實
當然,龍潭的肯納雙老家園並不是完美的。就像壽豐的肯納園是龍潭肯納雙老家園的前期實驗,肯納雙老家園也將是未來在這個世界上某一個角落裡一個村莊的先驅實驗。而美好的世界,也必然是這樣一步一步走出來的,不是嗎?
只是,在現實的過程當中,這個夢想的過程裡有太多不可預期的變數了。譬如,我曾經邀請淡江建築系劉欣蓉教授來幫忙,而她也十分熱情和慷慨地願意擔任義工,希望能夠讓這個即將形成的社區,不論在空間上或者是人的關係上,可以在前期做更多努力,讓將來的成功更有保障,讓整個品質可以有最大的提升。在我單純的想法裡,如果肯納雙老家園的計劃過程可以將很多的細節加進來,以後成功的機會會更大,複製起來也會更容易。
而這些細節,包括建築上應該招國際標,讓肯納雙老家園從籌備就開始有一定的知名度,這樣以後在龍潭的孩子們,就會有更多的機會接觸到聞名而來的一般民眾;也包括在建築上創造更多的社區互動空間,讓每個家庭都可以走出自己的屋間,增加更多的互動與交流。
然而,現實的世界裡,是這些肯納父母已經苦撐許多年了。每隔一陣子就聽到有某位家長心臟出了問題,或者某位得了癌症。許多陳義甚高的理念,終究還是要配合現實的條件來執行。

讓溫柔與堅毅來領路
肯納雙老家園整個看得見和看不見的工程,相當地困難和複雜,是很難複製的。但其中有一個促成大家一直一起努力下去的因素,就是董事長彭玉燕女士這樣一個人。
認識她將近二十年以來,聽她陸陸續續說了許多個人生命的故事,從楊梅到巴西再回到臺北,整個生命跌宕起伏的各種讓人驚險和扼腕的情節,其實是值得魏德聖這樣的導演再去拍一次三部曲的。整個肯納雙老家園在理想和現實的拉扯之間,在幾十個家庭從陌生到熟悉到必須要彼此信任的過程當中,從完全不可能到如今開始有了具體的樣貌,如果沒有彭玉燕女士這位客家女子,沒有她身上所具有的不可思議的毅力和柔軟,我敢說是完全不可能的。
這兩種極為不同的特質,甚至可以說是彼此矛盾的元素,就這樣展現在這樣一位看起來極其平衡的肯納媽媽身上。而這些年來我自己更投入於榮格的心理學理論,也越來越明白:只有事物兩邊的對立面能夠完成結合,才有了提升到下一個境界的可能性。
當然,肯納雙老家園不可能只靠彭玉燕一個人,還有許許多多的肯納家長默默的奉獻,特別是他們敢將整個家庭的未來,投擲在這個完全還沒看見的村莊上,這樣的信任是需要多麼大的勇氣呀!這樣的信任,以及五、六十個家庭都敢彼此信任彼此的勇氣,才有可能打造出來這樣的夢幻家園。
而我在這裡只是一個單純的參與者,精神科醫師的頭銜用不上,兒童精神科醫師也同樣用不上,頂多只是單純的見證者,見證著在過去臺灣沒有過的新的嘗試和新的勇氣,這真的是歷史的一刻!而這樣的見證本身,是一件多麼讓人感到驕傲的事情!
疫情以前,週末突來的閒暇,和朋友一起驅車又到了即將落成的肯納雙老家園,以及綠意盎然而廣大的有機農場。真的實在很難想像,這樣一個夢,超過十五年以上的努力,竟然開始有一個基本的雛形了。
肯納雙老家園將不只是臺灣歷史的一個新的里程碑,也是人類歷史上重新又學習互助和信任一次重要的具體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