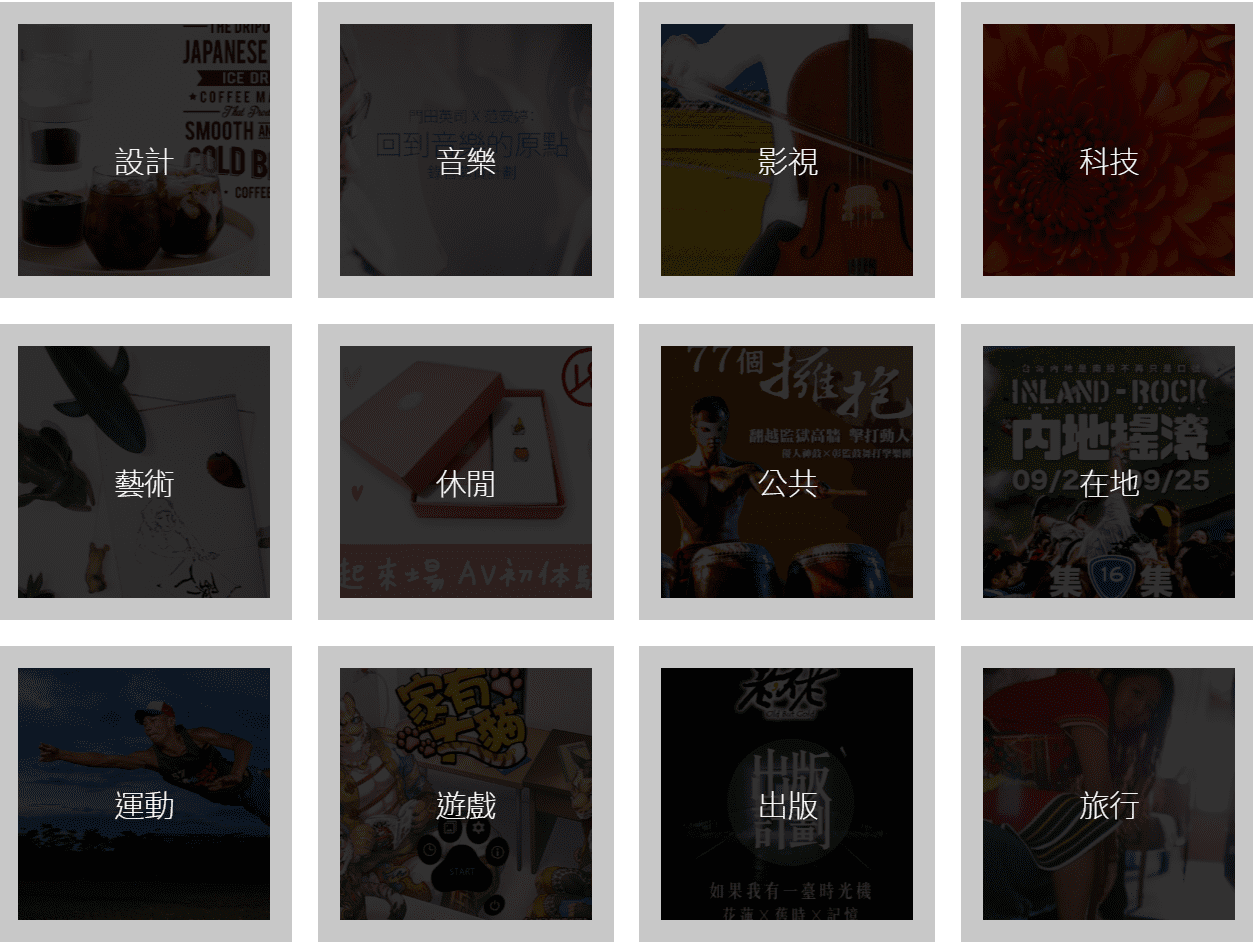【阿北望遠鏡】從《大誌》思考社會創新:讓「認知」先行,「態度」與「行動」緊跟其後
編按:
由專業國際 NGO 工作者褚士瑩坐鎮回答各種 NPO/NGO 相關提問的專欄【阿北私會所】轉眼就 2 歲了!今年開始,褚阿北與 NPOst 決定轉身探頭,向外觀察,從阿北在國際非營利組織擔任顧問工作的日常中,帶回國際間在社會服務領域裡,各種好玩、有趣的潮流與做法。這個從 2018 年開始的新專欄【阿北望遠鏡】要分享的,可能是一個小小的設計,也可能是一個巨大的野心,甚至是一個失敗的計畫或爭議的概念,但無論如何,都希望成為臺灣 NPO/NGO 工作者一種新鮮的思考。
ps. 雖然如此,【阿北私會所】精神不死,如果你還是有 NPO/NGO 相關的問題,還是歡迎舉手發問 喔!阿北心腸軟
又愛罵人,一定不會棄之不顧的!
最近因為臺灣的《大誌》(The Big Issue)雜誌,社會有了機會檢視一些早就存在的問題,像是引進臺灣的外國品牌時,到底可不可以跟英國的原生發展模式脫鉤?脫鉤以後的《大誌》,還算不算是社會企業?無論是經營者、販售者、社會學者,都趁著這次討論的機會,走出灰色地帶,站在自己的立場清楚做了選擇,長遠來說,無疑是一件好事。而我也趁此機會,在看完 NPOst 的討論會報導後,又想了一些。(參考:當《大誌》遇上「勞雇」、「社企」與「品牌」/「《大誌》、街友與勞雇的多元想像」活動現場)

12/18 的討論會。攝影/葉靜倫。
例如,關於消費者會怎麼想呢?一般不在 NGO 領域的消費大眾怎麼想?我趁這次機會,隨機問了一些同溫層以外不同族群的朋友,其中有一個年輕女性朋友,她的回答讓我覺得很有趣。
「我不會買《大誌》,但是我會買玉蘭花。」她不假思索的說。
「為什麼?」我緊接著問。
「咦?為什麼嗎?我沒有想過耶⋯⋯」她好像突然被問了一個類似「妳睡覺時手會放在棉被裡還是棉被外」的問題。
我們開始討論,為什麼同樣是街賣,她選擇買玉蘭花,而不會買《大誌》?
她從消費者的立場,找出了 2 個主要的原因:
- 賣玉蘭花的街賣者,感覺上比賣大誌雜誌的街賣者更「弱勢」。
- 玉蘭花這種商品本身,有時間的「緊急性」,感覺當天不賣完不行,但是雜誌可以賣一個月,比較不急迫。
這位工作與生活都自認為跟 NGO 發展、社會正義沒有直接相關的年輕女性,其實點出了 2 個關於「街賣」的重要關鍵:
- 無論我們是否願意承認,但在一般消費者心目中,街賣者的商品替代性其實很高,像是痠痛貼布、原子筆、抹布、玉蘭花、口香糖、手工餅乾,或是《大誌》雜誌等,都可以互相取代,購買的關鍵不是「需要」,而在於是否能被激發高程度的「同情」。
- 當商品不具必要性時,「同情購買」類型的消費者(占街賣消費族群的極大比例),會優先考慮商品的「時效性」(街賣銷庫存的急迫性,如同我們願意跟路上發傳單的老人家拿廣告單,很多時候是希望能幫他們一把,讓他們「趕快發完,趕快下班」)。
所以,如果消費者清楚知道,如同臺灣《大誌》創辦人李取中在討論會中所言,臺灣《大誌》的營運模式是「街賣者如果沒有將當月雜誌賣完,可以拿過期的雜誌換新一期的雜誌」,那麼,被「同情」與「時效性」所誘發的購買行為就會大幅降低。因為每月出刊的《大誌》雜誌,等於永遠不會過期,比起玉蘭花與口香糖,突然變得更沒有時效性/急迫性。
注重這 2 個條件的消費者,在購買同樣不是必需品的街賣商品時,自然就會轉向如玉蘭花這類同時符合 2 個條件的商品。
從市場機制來看《大誌》這個街賣商品
當然,以《大誌》的品質而言,如果用鮮花分級的話,在臺灣應該遠超過玉蘭花的等級,它比較接近文青喜歡的簡約風格,好比內外皆美,又帶著異國風情的日本茱萸。
在桃園機場的航空公司貴賓室裡,雜誌架立面也會擺放幾本《大誌》,在一片浩瀚精美的雜誌封面中,我都會因為《大誌》封面的質感,而一眼就注意到它,就是因為它擁有日本茱萸般優雅有型的「高階」形象。但如果販賣玉蘭花的街賣者,改賣貴氣逼人的日本茱萸,可能就賣不出去,因為玉蘭花的「低階」形象,跟一般大眾對街賣者「弱勢」的刻板印象,反而較能想像與結合。
所以臺灣版的《大誌》,如果跟英國原始的設計脫鉤,也就是說,它既不是消費者必須的商品,如今又(在那場討論會中)說自己不是社會企業,一來已無法引起過路人的同情或同理,二來街賣者也沒有急迫出售的時效性,那它還剩下什麼呢?
剩下的,就是非常純粹的「違法在街上販賣優質雜誌」了。

圖/Nikhiel CS @ Pexels
然而,「違法」跟「優質」的本質是相衝突的。不信的話,我們試著想想,在世界上,有什麼是「在街上違法販賣的優質非必要商品」?我想了很久,唯一想得出來的,只有阿姆斯特丹街頭常會有阿弟仔鬼祟兜售的「頂級有機大麻」。
但是一般消費者,有多少人會認為向街賣者非法購買優質大麻,是一件讓自己覺得光榮、愉悅,又有社會意義的事?這能算支持有機小農嗎?同理可證,拿掉社會設計,會有多少文青認為跟非法的街賣者購買優質雜誌,是一種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這樣還能算是支持無家者嗎?
雖然我並不贊成販賣同情,但是在同樣採用非法街頭販賣形式的前提下,否認自己是社會企業,否認跟街賣者的勞雇關係,並不等同於給街賣者「尊嚴」。且讓街賣者可以用過期雜誌換新雜誌,也不等於創新,只是將街賣商品的「急迫性」特質拿掉,這不是一種商業模式的改進,反而降低了消費者掏錢的衝動。

圖/Noralí Emilio @ unsplash
對於街賣者,長期來說,這個制度反而是種傷害。不信的話,我們試想,如果玉蘭花大盤商告訴大眾,他批給街賣者的玉蘭花,只要沒有賣掉,隔天全都可以拿來換新花。請問深夜在路邊、在夜店前向阿婆買花的人會變多,還是變少?這個「改進」,實質上會幫助街賣者,還是傷害街賣者的利益?
當然,依照臺灣的法令,街賣者無論販賣什麼合法商品,一律像是在阿姆斯特丹街頭兜售大麻那樣背負違法的罪名,並不是我們應該輕易接受的,但這是另外一個需要討論的議題了。
在法令有所改變之前,考慮種種街賣商品後,我這位年輕的朋友,排出了她遇到街賣者時,願意向其購買商品的優先順序:玉蘭花 → 手工餅乾 → 原子筆 → 《大誌》雜誌。
這不是什麼陰謀論,只是現實的市場機制而已。
社會創新,只有名字創新遠遠不夠
這幾年,在 NGO 跟社會企業的工作領域,我發現好像每個人都在說「社會創新」(social innovation)跟「設計思考」(design thinking),但沒有幾個人真正說得出那是什麼。這讓我深思,我自己在 NGO 這個領域工作 20 年來, 真的有做到創新嗎?還是說我們創新的從來都只有名字?
例如「樂活」,例如「社會企業」,例如「翻轉教育」或「地方創生」,最後都只剩下顧名思義的各自表述。多麼令人失望!到最後,樂活原來只可以拿來賣火鍋跟足療養生館,而臺灣的《大誌》原來不是社會企業。

圖/Ramdlon @ Pixabay, CC0 Creative Commons
在「我不會買大誌雜誌,但是會買玉蘭花」的討論隔天,我剛好聽到德國默克藥廠在「未來對話」系列的播客(Podcast),裡面有一集提到,一位設計核磁共振(MRI)機器的科學家到醫院現場實際觀察 MRI 的使用方式後,才發現很多小孩都害怕被推進那臺他精心發明(卻長得很像棺材)的機器裡,所以這些孩子必須進行原本不必要的麻醉,徒增年幼患者的醫療風險。
這位科學家這時才發現,自己在設計的過程中都只有想到功能,卻沒有從「使用者的角度」來檢視設計成品,所以他做了有創意的改變,讓小朋友覺得進去 MRI 機器猶如一場有趣的探險之旅,令人不快的困境也因此得以解決。
真正基於「設計思考」所引發的「社會創新」,必須圍繞著 2 個關鍵詞:「他人視角」,以及「創新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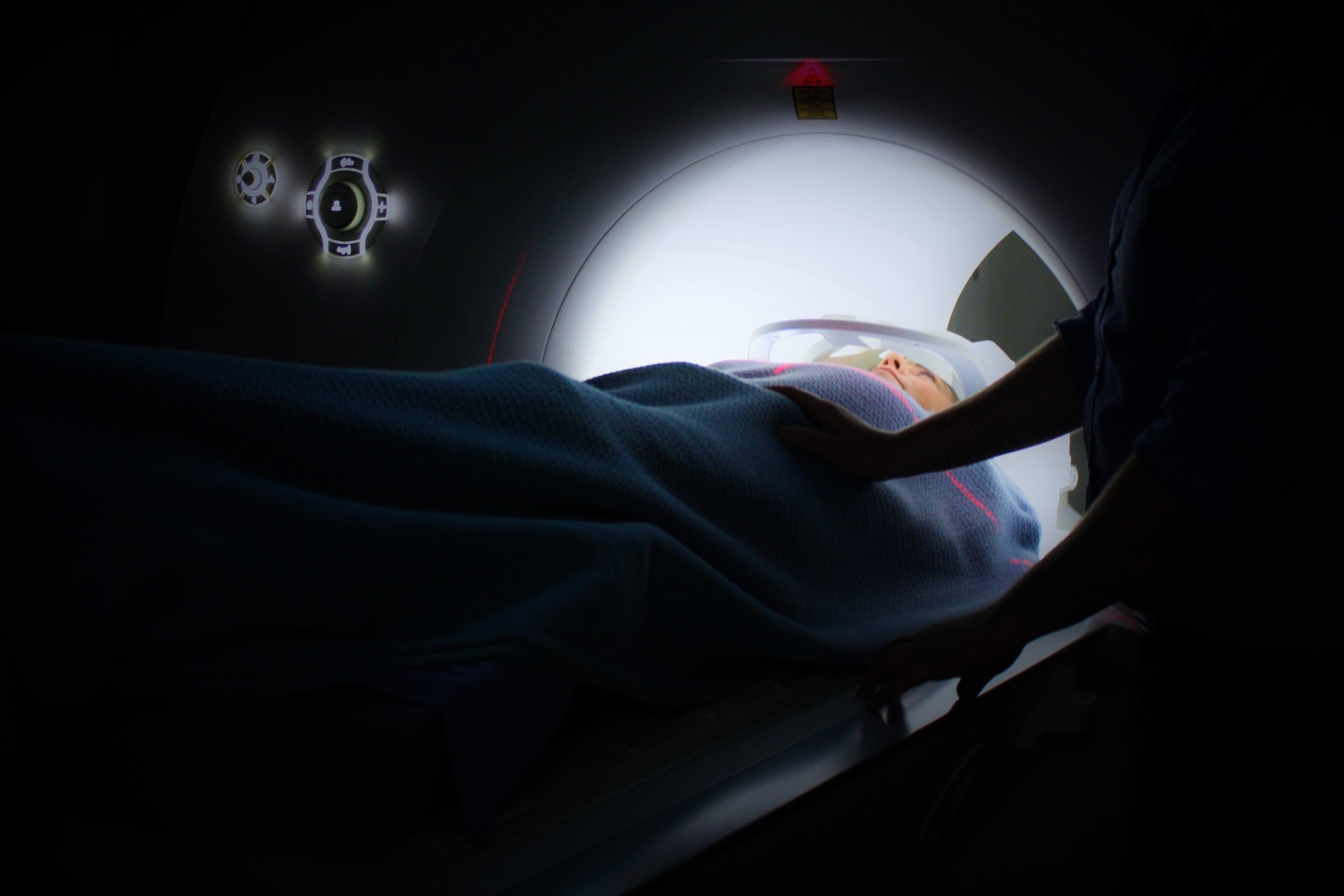
圖/Ken Treloar @ unsplash
社會創新:以「認知」為先,「行動」和「態度」緊跟在後
不管是不是社會企業,還是社會創新,只要能夠產生社會影響(social impact),都不能違背所謂的「ABC 規則」:態度(Attitude)、行動(Behavior) 與認知(Cognition)。而這 3 者在我心目中,又以「認知」最關鍵。如果創業者對「社會問題」、「成功創業」、「創新方法」3 方面的「認知」都過少,那麼就算有「態度」、有「行動」,也會被社會的現實潑一盆涼水,因為消費者不會買單!
認知缺乏的創業者,為了要活下來,總會找到充分的藉口,最常聽到的前 3 名不外乎:「大環境太差!」、「體制太爛!」、「資源太少!」
但事實真是如此嗎?因為資源不夠,便能理直氣壯引進國外已苦心積累下社會信任的原品牌來用嗎?想賣漢堡但沒錢自己做品牌,就可以把漢堡取名叫麥當勞嗎?正因為做品牌確是如此艱難的事,我們才要如此敬重英國好不容易做起來的原品牌,並且不希望它在臺灣被誤解。
「我能怎麼辦?想辦法先活下來再說吧!」一旦自我合理化之後,社會行動者就會忘記初衷,忘記當初是為了解決什麼問題才開始做這件事,原本一心想著要做的創新,因為冒然行動與設計不良,現在只剩下東貼一塊狗皮膏藥、西補一條矽利康(silicon)的補丁痕跡,而原本滿腔熱血的實踐者,便輕易拋棄了原先美好的態度,採取偏離初衷的行動,進入求生模式,還誤認為全世界都在跟自己作對。

圖/Christina Morillo @ Pexels
關於設計思考,我們需要更多的社會性
有沒有解方?有的,那就是用「設計思考」打掉重練。
設計思考並不是一個全新的理論,其實幾十年來各種業務人員、研究員、設計師等都套用著大同小異的流程,比如說為了找到目標客戶(TA),通過訪談或者消費者民意調查來釐清客戶需求,再根據客戶需求進行設計,生產出一個產品的 beta 版(第一個對外公開的版本)讓顧客參與測試,接著根據測試結果進行改進等。只是這整套方法,沒有特別納入「設計思考」的系統裡。
但既然有了專有名詞,表示一定也有關鍵突破點。設計思考的突破點在於,設計領域有史以來,第一次強調設計師必須以「具體的對象」和「對象身處的情境」為主體,著手設計產品以及銷售、利潤分配模式,而不能像過去一樣,只將關注的重點放在產品的技術提升、市場占有率、分析競爭對手等傳統商業角度中。簡言之,必須對即將使用這個設計的人,對其生活情境,有誠摯而深刻的「認知」。
比起設計一張沙發、一棟房子,設計應該關注人的「社會領域」,然而這種以「認知」為主體的設計,卻停留在幾乎蠻荒的階段,很多社會行動者要不是不知道,就是即使知道也無法付諸實踐,如同資本社會在面對外籍移工時,產生了「我們只想要一雙手,卻來了一個人」的尷尬。

圖/Nikita Kachanovsky @ unsplash
無關對錯,而是忽略自身影響力
平心而論,臺灣《大誌》沒有「做錯」什麼,而是沒有「把對的事做好」。就像人力仲介沒有捍衛外勞的權益、伊甸基金會沒有幫復康巴士司機繳付因為停紅線載身障使用者而被開的違停罰單,或是政府沒有照顧無家者,卻對迫於生計而做街賣的無家者開罰單。而我們想問的是,有沒有可能「做對的事」,同時又「把對的事做好」?當然可以,外勞仲介、伊甸基金會、政府,都有能力這麼做,也都可以這麼做,卻「選擇」沒有這麼做,臺灣的《大誌》也一樣。
既然有能力把對的事做好,卻沒有做,當然不是因為惡意,而是因為對自己造成的社會影響,認知不夠。
我期許社會領域的每一個實踐者──包括我自己在內,都能夠藉由這次對於臺灣《大誌》的討論,學習、應用設計思考的核心精神,在每一次的設計中,以「認知」為先,對議題有清楚的認知後,確認自己深入理解其「社會性」、知道如何以此「成功創業」,並且大膽設計出符合使用者需求的「創新方法」。
有了這 3 方的認知,再來重新安排優先順序,讓「行動」和「態度」緊跟在後,才能完成一個合理、有效而美好的社會設計。
延伸閱讀:
褚士瑩:社會企業並不是解決社會問題的萬靈丹,社會參與最重要的是「態度」/《社企是門好生意?》推薦序
當《大誌》遇上「勞雇」、「社企」與「品牌」/「《大誌》、街友與勞雇的多元想像」活動現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