溯洄從之,道阻且長:合作在他方/主婦聯盟合作社推動勞務承攬爭議(後記)
承上下篇事件爭議始末:框架之外,「尊嚴勞動」可能嗎?、站在合作的分水嶺,勞工為什麼「不選擇」?
「合作社裡最大的成本是什麼?不就是溝通的成本嗎?」9 月,在一夕入秋的臺南,我帶著主聯事件始末去訪問臺灣勞工陣線主任洪敬舒。再過 2 個小時,他就要對著一群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的社員談「合作的艱難」。「合作經濟裡最好的、最可貴的,就是民主參與、民主治理,你願不願意花時間去參與?花時間去溝通?缺少了這個,就和一般企業一點差別都沒有了。」
在訪談主聯合作社此次事件雙方當事人的過程中,最深的感受,就是兩造業已沒有有效的溝通渠道,取而代之的,莫名其妙地受到信任的,反而是各種想當然爾的人際網絡:某成員是資深工作者,他一定懂我們的用心;某員工就跟我在同一個辦公室裡、文件都是他幫忙做的,他怎麼可能不知道我們新修改的方向?某理事是我的朋友,他應該要理解我們只是在維護權益……
望向兩端的合作想像
於是數月過去了,在一個有合法勞方代表的合作社中,除了幾場更激化事態的「說明會」,工會寧可朝著外面說話,而社方沉默以對。「我們並不是沒有在對內溝通,我們是把力氣都留下來和合作社的社員對話,讓社員了解方案的內容。」合作社理事陳郁玲說。但是,如果這是一個發生在勞資關係裡的衝突,其實真正急需對話的,是社方與職員。

圖片來源/主聯合作社工會粉專
我帶著同樣的問題去問工會常務理事章雅喬,她說:「妳不能檢討資源少的這一方。今天社方才是有行政資源的那個,我們要上班、要工作,工會幹部都是擠出自己的時間來討論開會,而且社方改了什麼、準備要怎麼改,都是只有他們才知道啊!」蔡一維說,他每個版本都有寄給職員們看,但在工作者這一端,只覺得那是「一個 Excel 檔案裡面,一堆數字」。
缺少有效的、好的溝通渠道,不斷衍生的猜疑和戒慎使得互信基礎變得更加薄弱,遂成為一個「做的人冤,聽的人忿」的局面。工會在回應社方的方式上,踩了傳統企業中勞資對立的立場,在工會發出的一個聲明與 2 版懶人包中,都將「消費合作社欲推動勞動合作社」這件事描述為人力外包。這若從習以為常的勞資關係想像中來看,某種程度上,將既定的業務交予他人承攬,要說是外包也沒有錯,只是這個從傳統勞務關係中抓下來的詞,並不足夠能公平地描繪勞動合作社的輪廓。
虛假或退化的「合作」,比傳統雇傭關係更危險
勞動合作社就是以專業技術、以勞動力去承攬勞務,所以差別在哪兒呢?唯「自主」二字矣。工時的自主,工作內容的自主,工資的自主,工作方法的自主。
這也是另一個社方與工會在認知上截然不同的爭議點。工會主張「我在你的場域,賣你指定的商品,雖然沒有直接受你管理,但是在承攬費用公式中,業務獎金的設計仍是一種將管理績效等名目包在裡頭的方式,這樣怎麼能算是勞務自主呢?」然而,回到勞務承攬的性質來想,合理的績效要求、指定販售商品與工作方式,與其說是不自主,其實比較接近兩造合意契約內容的議定。
一個可以自己決定工時、自己決定工資分配方式,也可以決定承接誰的勞務的「合作社」,我認為即滿足了「勞務自主」的條件;而在因承攬他人業務而與另一個主體產生關聯的層面上,滿足若干要求與受其指揮,是屬於業務所需,在業務層次上的「無法全然自主」,並不會直接否定了勞動合作社在經營上的自主性。

圖片來源/主聯合作社粉專
這個對於「自主」的想像,其不同層次的紊亂,至少在職員這一端,揭露的其實是許多受僱者在不熟悉合作經濟的情況下,勞務自主、尊嚴勞動,從來就不是一個職涯選項。想到勞務承攬,只能想到外包;想到外包,只能想到雇主要規避責任,由此而生,則更值得探問的,反而是主聯合作社由上而下、由中央而地方,嘗試以消費合作社的現有資源來催生勞動合作社,並且還讓這個催生的實踐,直接發生在現存的真實勞資關係場域中。然而,有勞資關係的地方,就有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如此一來,這個充滿意義的嘗試,會不會有可能與合作社核心價值「自願結合」背道而馳?
這是一件可怕的事,也是一個令人不忍的念頭。偽合作社比資方更危險,正因若將「合作意識」與「自願結合」從組織中剝除,在現行缺乏監核與自律機制的環境下,「玩假的」勞動合作社可以對勞動者造成比企業更大的傷害,因為在勞動合作社這個架構下工作的人們,甚至不是「勞工」了。
是以,合作經濟中人與人的結合,不僅只是在道德上希望他們彼此充滿合作的意願,而是在務實面,他們也非充滿意願不可。有合作意願,才有了合作意識,才會相信花在溝通與理解對方的時間不是白費,才會相信民主與平等最終會更有效率。那麼,是逆水行舟?是順水推舟?還是水到渠成?我們該怎麼評價主聯合作社所做的嘗試呢?

圖片來源/主聯合作社官網
職員這端的需求是存疑的,社員那端的需求則可能才更是社方著意推動的主因。雖然在採訪過程中,工會幹部不斷提醒我:「根本就沒有人知道什麼是勞動合作社。如果你站在站所一整天,問每一個走進站所的社員說,『你知道社方要推勞動合作社嗎?』,他們大概都會一臉迷惘,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
諷刺的是,如果到最後真的都沒有人要出來組成勞動合作社承攬站所業務,如果這個「需求」真的是社方虛構的,那麼工會與基層勞動者所憂慮與恐慌的工作權益受到影響、甚至是被取代的問題,亦於焉不存。
沒有典範的先行路上,協力生活的理型是什麼?
在訪談過程中,幾乎每一方、每一個人都同意的一件事,是此事之難,難在前方完全沒有典範的存在。沒有成功的經驗,某種程度上就是要人閉眼走入深谷,那豈是覺悟或進步或教育足不足夠的問題?那幾乎會演變成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矛盾。成功的典範是如何從無到有誕生的?應先培植土壤,改善環境,應該埋頭再做 10 年、20 年、30 年的合作教育?還是要先把小鷹帶到懸崖邊,要牠相信自己可以飛?
該耐心等下去,還是該往前跳一步?我沒有答案。

圖片來源/主聯合作社官網
事實上,推動站所轉型為勞動合作社,風險最大的其實是社方──高達 9 成的收入來自於站所,這意味著這一步如果跳錯了,經營許久且穩定成長的合作經濟體也會受到莫大的傷害。在日本生協的前例中,相似的事件甚至造成 45% 的退社潮。陳郁玲說,她覺得這是工會運動和合作社運動的差異,而今非常相似的駁火發生在臺灣,只是火花之後又該朝向何方?
合作社運動和工會運動有衝突嗎?洪敬舒說:「合作社裡的勞雇關係,當然還是回到勞資關係裡來談。今天工會就是一個合法的勞工代表,你不能當它不存在,這是行不通的。」做為合作經濟的研究者,同時也是勞工組織的幹部,洪敬舒認為,合作社裡若已然存在傳統的雇傭關係,就應該回歸勞基法的層面。
「有一個可能更有意義的問題是:為什麼合作社裡會長出傳統的雇傭關係?在國外,工人合作社,或基於特定專業而起來的勞動合作社,他們可能會朝外聘請專業經理人來代為執行某些業務,但是在主聯的例子中,目前受到影響的這些勞工,他們是專業經理人嗎?那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停下來思考,這種雇傭關係是怎麼在合作社裡長出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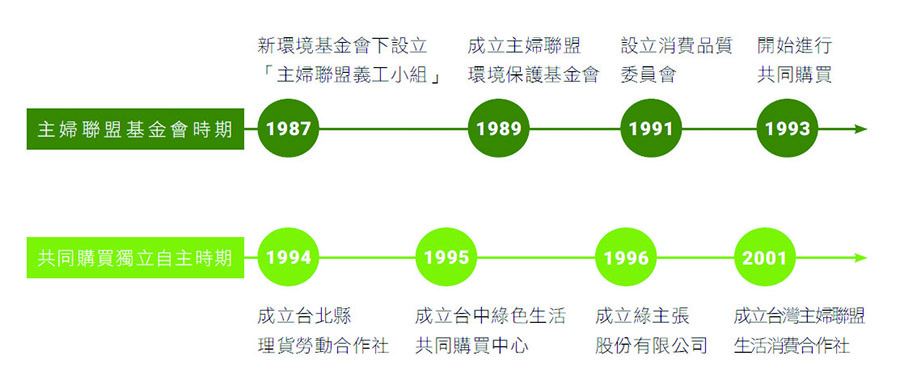
圖片來源/主聯合作社官網
事有前塵。在很多年前主聯合作社或許就面臨過一次歷史的岔路,當時的選擇,在發覺並不理想後,再要回頭收拾,就得面臨更深更重的阻力。在洪敬舒講完《合作的艱難》當晚,我和陳郁玲又站在騎樓底下聊了一會,她對我說,主婦聯盟不得不承認,自己對於社內的合作教育是失敗的。我卻始終認為,如果一個社會裡從來沒有任何人在談合作教育,如果一個勞工從來沒有任何管道去想像合作經濟,那麼這失敗的責任顯然屬於群體,全都放在主聯合作社身上也並不公允。
鄉民有句話說,潮水退了才知道誰沒穿褲子,在主婦聯盟消費合作社目前的處境上,我倒覺得是一場洪水襲來,才知道原來地基並不如自己想像中堅實。這起事件可以有的正面意義,大抵就是讓關心或有志從事合作經濟的人共同思辨:協力生活的理想樣貌是什麼?尋求共識需得跋山涉水,需得面對他人與己身的多重侷限,需得重建信任、重啟對話,修護受到損傷的關係,需得引人入勝。這麼難的道路,這麼曲折的旅途,我們能如何攜手共進?
延伸閱讀:
主婦聯盟環保基金會賴曉芬:「參與式民主的價值,正在於它的慢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