壽命延長了,卻更接近死亡?無效醫療的瘋狂與無知/《理想的告別》書摘
編按:
左岸文化於 2017 年 7 月出版《理想的告別:找尋我們的臨終之路》,作者安・紐曼(Ann Neumann)原是媒體編輯,為了罹患癌症的父親辭去工作,投入照護行列。
紐曼的父親最後在醫院死去,即便她原本想要協助父親在家裡好好終了。在那之後,紐曼不斷思索死亡的意義,更確切的說:何謂「善終」?我們能不能「有尊嚴」的死去?
臺灣將於 2025 年邁入「超高齡社會」(65 歲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比例達 20%),若以平均壽命 80 歲計算,每個人將有近乎(甚至超過) 15 年的老年生活,生死之間並非秒瞬之隔,而是一段漫長的旅程。
本篇為此書的第 3 章「無價的日子」,勇於直白談論死亡的紐曼寫出人們如何將面對死亡的恐懼堆疊成他人巨大的苦痛,不僅如此,無效的過度醫療不僅造成全民經濟的龐大負擔,對病患而言,日夜承受著身體與情緒的苦難,不如好好的死去。
文/安・紐曼(Ann Neumann) 譯/胡訢諄
歷代都有人提出勸戒,不宜對患者過度治療。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的醫學教授施奈德曼(Lawrence J. Schneiderman)在其著作《擁抱死亡》(Embracing Our Mortality)中便提到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的警告:「凡病入膏肓、已無可得的治療方法,醫生就不得期待藥物能夠克服疾病⋯⋯意圖行使無效治療,即是與瘋狂為伍、展現自己的無知。」
「無效」(futility)意味枉然、無結果、無用,終究帶來極度的失望。無效治療就是無法拯救生命的醫療手段。根據希波克拉底本人與弟子整理的文獻(約為公元前 450 至 350 年),治療無法被治癒的病人是「瘋狂」的行為。施奈德曼也提到柏拉圖《理想國》裡的良醫:「對於長期的內科病患,傳奇的醫神阿斯克勒庇厄斯(Asclepius)就不會開立處方,那只是延長他們痛苦的生命⋯⋯受到疾病纏身也無法工作的生命不值得存活。」

圖/Daan Stevens @ Unsplash
1960 至 1970 年間,科學家陸續發明各種延長生命的方式,人類反而越來越難避免過度治療或延長病人痛苦。彼徹姆(Tom L. Beauchamp)與查德里斯(James F. Childress)在著作《生物醫學倫理原理》(Principles of Biomedical Ethics)中,定義無效治療為「表面上有治療的義務,但其實各種條件都不成立」。該書於 1977 年出版,是醫學領域的重大里程碑,在科技競逐發展的年代,首度有人嘗試建立醫學倫理。
他們寫道:「基本上,所謂『無效治療』的意思是,對於無法挽回之瀕死病患,我們給予進一步的治療,但這對他們的生理情況毫無助益,也無法帶來任何希望,因此是非必要的行為。」無效照護的概念應該不難理解,數世紀以來沒什麼改變,包括無法(或不再能)治療致死疾病的手術、藥物等醫療手段。然而什麼照護才是無效的,往往很難決定,要取決於許多因素。

圖/Piron Guillaume @ Unsplash
壽命延長了,卻更接近真正的死亡
其中一個因素是我們對死亡的恐懼,除了身體的疼痛,相關的一切都讓人害怕,例如拋下親愛的人、失去對身體的控制、自己所知的世界將消失。無論你的信仰有多堅強,死亡跟所有神秘的事物一樣令人害怕,即使你相信人生有希望、相信有天堂、相信死後有更好的境遇。我很少遇到瀕死卻不懷疑死亡意義的人,無論是基督徒、無神論者或其他信仰的人。(我遇上的安寧療護病患,身體總是不舒服、非常痛苦,幾乎每個都說想死)
對於死亡的懷疑與害怕非常普遍,也很正常,數十年來的科學發展更助長這種念頭,科學家給我們希望,承諾可以「治癒」老年、緩和死亡。我們生活的這個年代,死亡並不真實,那是發生在別人身上的事情,於是我們騙自己,死亡是可以避免的,在癌症、阿茲海默症、腎臟病找上我們之前,人類就會找到解藥。人的壽命的確延長了,我們因此上當,以為可以閃躲死亡,長生不死,甚至開始很少想到死亡。

圖/Silvestri Matteo @ Unsplash
偽善的醫療
巴特勒在回憶錄《偽善的醫療》(Knocking on Heaven’s Door)中,描寫年逾 80 的父親失智、肢體無力,病情每況愈下,她卻無法關掉他的心律調節器。她也提到,就連沒有根據的希望,也會干擾醫療決定。當前的醫療是以治療而非照護為目的,她的著作詳實記錄著,如果病患拒絕這種醫療,需要面臨什麼挑戰。她的父親中風後,在復健的過程中發生疝氣。醫院告知,儘管年事已高又患有重疾,父親仍必須安裝心律調節器才能進行疝氣手術。巴特勒寫道:「我父母考慮的不只是心律調節器。他們想的是,要承受多少痛苦,才能換得人世間多幾年的相處。而且他們不知道答案。」每日的照護加上漫長的過程,終究吞噬這個家庭。

圖/rawpixel.com @ Unsplash
生物醫學倫理專家莫曼(Margaret E. Mohrmann)醫師在《論道德醫學》(On Moral Medicine)中,描述希望的力量以及它如何衝撞醫學。莫曼服務的兒科加護病房有個孩子傑梅被診斷出致命的神經退化疾病。傑梅和姊姊相差 20 歲,父母亟欲救他,於是帶他到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尋求其他意見。傑梅在研究院停止呼吸,家人之前沒有決定怎麼照護他,所以研究院的醫生進行插管急救,管子從他的嘴巴插進氣管,再接上呼吸器。不久之後,這對父母想把孩子轉回莫曼工作的地區醫院,不僅離家近,又有親友與教友陪伴。
莫曼發現,傑梅的父母不僅希望孩子活下來,也在等待神為他們下決定。他們認為,儘管孩子緩慢的邁向死亡,卻不感到疼痛。他們給上帝治療的機會,時間恰好就是看似治療無望的時候。莫曼問那對父母,他們認為上帝會如何處理?嚴重的感染?心臟衰竭?他們告訴她,會將這些視為上帝準備帶走傑梅的表示。「對傑梅的父母而言,最重要的是,將來他們能夠記得,在生死奮鬥之際,自己對傑梅和上帝仍然深具信心。」幾天之後,傑梅死於心臟衰竭。
傑梅的故事顯示出,無效治療的定義是什麼,我們並沒有共識。只要一考量病患身邊每個人的需求,醫療的效益就要擴大到家庭、社區和醫護人員。然而,莫曼能夠擴張無效醫療的定義,只因傑梅還小(所以在他身上做各種嘗試似乎合理),以及他不感到疼痛。

圖/Natanael Melchor @ Unsplash
取得治療很容易,拒絕反而比較困難
要是我們把疼痛和苦難一併納入無效醫療的花費呢?若考慮疼痛的代價,又要如何追求每個人的善終呢?目標會改變嗎?我們遇到新的數學題,不僅要考慮臨終照護的金錢花費,還要考慮體力與精神的損失。更嚴重的是,我們不只把珍貴的醫療資源用來折磨瀕死的病人,還因此損害非瀕死的病人利益,後者的生命原本有機會獲得改善與拯救。就許多方面來看,迫使瀕死病人接受無效的檢查與治療、避談沉重的話題、無視疼痛的代價,等於否決其他人的生存機會,剝奪他們的資源。
2013 年,記者麗莎‧克里格(Lisa M. Krieger)在《聖荷西水星報》(San Jose Mercury News)以特稿寫出她父親過世的故事。克里格記錄父親去世前 10 天的花費,總共是 32 萬 3658 美元(約 963 萬元臺幣)。
肯尼斯‧克里格 88 歲,曾經是工程師,患有失智症,同時因細菌感染引發敗血症。他做了一切他以為臨終必要的安排: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以及「希望自然死亡」的法律聲明。但某個星期六,他的健康狀況惡化──「全身發抖,脫水,胡言亂語」──緊張之下,克里格火速將他送往附近醫院的急診室。醫師開始長達 10 天的檢查,包括照 X 光,讓他服用藥物,但這些事都讓她父親很困惑,醫院的環境更令他難過。

圖/rawpixel.com @ Unsplash
當時她沒有考量到花費,有可能想那些嗎?眼睜睜看著父親疼痛、神智不清,克里格帶父親到加護病房、簽名同意一系列的檢查之後,她問自己:「一個 88 歲、孱弱、心律不整、失智的人,撐得過嗎?如果他活了下來,又會變成怎樣?」工作人員建議她讓父親接受手術。「所有專科醫生離開後,我打起精神,攔住主治醫師,問他:請你告訴我,接下來會怎麼樣。」主治醫生的評估並不樂觀,克里格最終沒有接受手術建議。她寫道:「取得世界級的治療很容易,拒絕反而比較困難。」
為了避免死亡而付出代價
我們全體不惜一切代價避免死亡。我們全都是共犯,促成 50 年來社會的痛苦與龐大花費。無效醫療像一個漏斗,把資源從需要的人身上取走。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美國 10 大死因依序為:心臟疾病、癌症、肺臟疾病、中風、意外(非故意傷害)、阿茲海默症、糖尿病、腎臟疾病、流感與肺炎、自殺。由於美國人口平均年齡快速上升,越來越多健康照護資源用於控制老年慢性疾病。
2009 年,美國 65 歲以上的人口是 3960 萬;到 2030 年,將會增加一倍,到 7210 萬人。摒除自殺與意外,死亡已經成為漫長的過程,包含一連串的醫療手段、藥物療程和實驗,雖然我們不清楚那是在消滅還是延長疾病。由於兒童死亡率下降、手術感染改善與疾病治癒率提高,現在的美國人壽命大概是 19 世紀初的 3 倍,但多出來的幾年卻不是我們想要的黃金退休人生。

圖/Hush Naidoo @ Unsplash
這些數字的提升就金融上來看是龐大的經濟災難:2010 年,美國人花費 2.6 兆美元(77.4 兆元臺幣)於健康照護,占 GDP 的 70% 以上,是 2000 年的 2 倍。不過,全部支出有一半花在僅 5% 的人,約 1/3 的醫療費用都花在病患的最後一年。
我們很難不去思考,花在肯尼斯‧克里格身上的 32 萬 3658 美元,可以用在哪些別的地方:它至少是 250 人一年的醫療花費。此外,那些錢也可以在紐約非營利醫院的加護病房住 170 天,或者讓 32 個寶寶出生。美國第一所生物倫理研究中心黑斯廷斯中心(The Hastings Center)的卡拉漢(Daniel Callahan)告訴莉莎:「我們必須瞭解,這場抗老戰爭不能無止境的延續下去。」

圖/Fabrizio Verrecchia @ Unsplash
有尊嚴的死亡,拒絕延遲苦痛
我們知道自己的痛存在,卻常常無法相信或接受別人的痛。史卡利(Elaine Scarry)在著作《疼痛的身體》(The Body in Pain)寫道:「疼痛是最確定的感覺、最鮮明的念頭。然而『他人的』疼痛卻非常難以捉摸,總是令人懷疑是否存在。」她告訴我們,那是因為感覺痛的時候,往往沒有表達痛的能力。疼痛令人無法說話,令人回到「人類還沒學會語言前的哭叫」。
然而,生理的疼痛絕對不只是身體的,也是精神的,或用安寧療護的措辭來說,是「存在的」。一旦我們長期疏忽痛苦,便會導致憂鬱、破壞人際關係、喪失安全感,並改變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但「疼痛是自然的,死亡可以延遲」,這樣的意識型態仍存在健康照護的經濟結構中。巴特勒在《偽善的醫療》寫道:「在這個系統下,我們不鼓勵『拒絕』,甚至連『考慮一下』都不行。」醫生不跟病人談生理和情緒的痛苦,只提無法治癒的治療方法,那只會增加病人、家屬、照顧者的折磨。
過去 50 年來,隨著醫學進步,人們已開始試圖終止不斷的過度治療與臨終前不停息的苦難。有些人說,推動立法、讓相關單位能協助死亡,病人才有權決定醫療手段、加快臨終的腳步,省去不必要的痛苦和折磨,包括失去身體、心智和一切事物的傷痛。發起者稱此為「有尊嚴的死亡」(Death with Dignity),不管你的生命僅剩 6 個月甚至更少,都應有法律權利,向醫生取得致命藥物的處方。這涉及的政治層面非常複雜,目的是給予因疼痛而無法發聲的病人表達的權利,逐漸獲得全國民眾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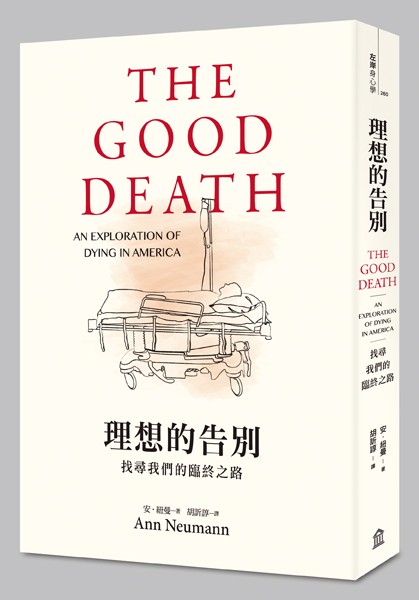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