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善究竟保護了誰?/《新慈善與社會正義》書評
文/洪瑞鷹
隨著全球政經、科技、人文、社會環境變動,慈善助人的領域也從過去單純伸出援手,轉變成積極意義更強的社會結構轉型。然而,慈善與民主這 2 組概念經常處於辯證關係,慈善利他的本質可能有助於民主社會中強調的自由平等原則,但慈善的代理人或中介組織,未必總是能促進實質上的社會正義,而且國家可能逃避了應有責任,必須打上一個問號,這是本書所欲處理的核心研究議題。
本書(見文末書籍資料)作者與編者貝魯茲・莫瓦瑞迪(Behrooz Morvaridi)目前服務於英格蘭中部的布拉福大學國際發展研究中心,而此書的出版社 Policy Press 也值得一提,該學術出版社專門以印行社會福利、社會學、社會工作、公共政策等專書,也跟倫敦政經學院的社會排除研究中心(Centre for Analysis of Social Exclusion, CASE)、英國社會政策學會、英格蘭社會學會有長期合作關係,致力於探討社會科學重要議題。

圖片來源/https://goo.gl/HhvxXi
慈善思維必須與時俱進
本書分成引言、新慈善與社會轉型的政策史、慈善資本主義與福利商品化、慈善與社會保護,以及全書結論等 5 部分來進行概念上的政策論述。主文計有 11 個章節,邀請了慈善研究領域的重要學者,圍繞此議題進行正反辯證。這類社會政策辯論,不只對於中央政府如衛生福利部、地方政府社會局處在社會立法有重要意義,對於企業部門、第三部門在實務運作同樣具有啟發。以中華社會福利聯合勸募協會的社福團體補助原則為例,掌握新慈善的正確方向,必須更積極思考如何有效運用善款、促進社會扶貧、確實協助弱勢家庭,才能促進社會共好的核心價值。而許多企業型基金會,例如台新銀行、國泰集團、中信金控、震旦集團、台灣大哥大基金會等,也逐漸理解到,社福團體缺的不只是有形資源,更需要透過各種培力合作形式,使基層弱勢亦對生命充滿盼望。
一位傳統社工系或社會系的學生,對於社會福利的相關概念並不陌生,舉凡社工 3 大工作方法,個案工作、團體工作與社區工作,或是社會學強調的結構性因素,經常可在各類教科書上一再提及。邁入 21 世紀的第 2 個 10 年,全球化對於慈善的實務運作也產生影響,近來國內外屢屢看見如公益創投、策略慈善、慈善資本主義、社會企業等字樣,就像企業管理的詞彙大舉入侵社福界。

圖片來源/https://goo.gl/EtuL1U
其中最值得反思之處,是越來越多「超級大富翁」投入慈善行列,例如微軟的比爾蓋茲、投資者華倫巴菲特、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伯等,正面支持者相信其善舉將打破舊有慈善「點對點」的單一模式,將更有效率的進行大規模社會改革;反對者則認為此舉更凸顯了全球財富過度集中於少數人手中,富人並未從根本解決社會問題,只是新自由主義下的扶貧策略,國家更可能藉機刪減社福支出,逃避政府應盡之責任。
為何而捐?傳統慈善注重「動機」
人性本善論者相信,人與人之間的相處乃基於信任,傳統慈善家認為財富的積累,可以幫助更多弱勢朋友翻轉生命。第一章的作者康寧漢(Hugh Cunningham)從歷史角度爬梳了近代西方慈善史,從慈善的英文字首「phil-」即意指愛人、促進人類福祉之意。英格蘭在社會福利的演變過程中,是從伊莉莎白時期殘補式的社會濟貧、逐步邁向二戰後的福利國家,由國家全面提供從出生至死、無所不包的福利服務模式。
到了工業革命時期,馬克思已點出資本家與勞工的階級對立與衝突、葛蘭西也指名慈善只是資本階級霸權的統治工具;布爾迪厄則質疑富人任何號稱具有善意的捐贈行為,不過是為了求名,以在社會中取得更多文化與符號資本。誠然,從「動機論」來探討慈善,人們一個簡單的捐贈行為背後往往隱含了許多目的,可能是回饋社區、為了節稅,或是宗教與政治上的考量。第 3 章的作者卡麥隆(Samuel Cameron)也用理性選擇論的經濟分析,說明捐款未必是利他主義,更多時候是恢復內在心靈平靜的自立考量。使得利己與利他二分法,在人群服務實務上不易釐清。

捐了,然後呢?新慈善講究「成果」
新慈善之所以「新」,其關鍵在於不問動機,而以「成果」論英雄。透過有形或無形的福利資源移轉,加上社工專業提供支持與關懷訪視,寄望案主或案家可以有不一樣的未來。無論是宣稱要解決非洲的瘧疾危機、拉丁美洲的教育斷層、東南亞的微型貸款,還是先進國家的長期照顧,新慈善不問捐款人這一筆鉅額捐款的真實目的,而看該筆資源投入後的預期產出、實際發揮的社會影響力,以及是否真正解決社會問題。
面對當代複雜的社會議題與成因,第 4 章的作者派爾(Tom Parr)點出一個新慈善時代的課題: 慈善是需要被教育的,我們卻誤以為人們生下來就知道如何有效行善。即便是經營企業有成的商業人士,也可能在經營慈善議題上一無所成,或投入過多資源錯置,甚至與政府資源重疊。
行善與賺錢可以並行?商品化的新慈善
本書第 2 章作者為公民社會知名學者麥可愛德華(Michael Edwards),他持批判立場來抨擊新慈善的過度包裝與操作,把社會福利市場化、商品化,化約式的商業邏輯使市場經濟只生產「能夠獲利的」產品或福利服務,而不是社會弱勢真正負擔得起的生活所需,原本應該在地脈絡與社會鑲嵌的元素,變成中央製造與通路配送。
愛德華認為,超級富豪們逐漸形成「矽谷共識」(Silicon Valley Consensus),奠基於過去在商業或高科技公司的成功經驗,誤以為科技與現代管理方法可以解決所有的社會問題與全球貧窮,一切都是「可以搞定的」,就像工程師編寫程式碼除錯。再者,擁有矽谷共識的企業家認為,慈善不再是捐贈者與受贈者的關係,而是經營事業與投資的關係,做好事應該獲利,而且行善與賺錢可以同時進行。

圖片來源/https://goo.gl/2pXoFb
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在這類質疑聲浪中,新慈善的發展力道失去了價值,只剩下價格。在慈善資本主義與社會商品化方面,本書第 5 章作者以南智利的個案研究實例說明,新慈善猶如一把雙面刃,不是社會轉型的終極救星。儘管社企創業家或慈善家最初宣稱要保護智利的生物多元性與自然保育,但在發展生態旅遊、並把環境保護當成一項旅遊業的「商品」來販售時,當地社區民眾不一定獲利,反而深受捐款人或旅客控制。此外,第 6 章作者則以非洲農業的例子說明,新慈善家還有正當性(legitimacy)不足的問題,當這些超級有錢人投入大量資源至當地社區,也許確實改善了小農人民的生活,卻繞過了當地政府、國會,之後誰來課責?誰來徵信?誰來公布有第 3 方公信力的財務報表?這樣的「砸錢慈善」是否能夠永續經營?
上述關於慈善議題的討論,不得不回到把政府角色拉回新慈善議題中進行思考。在第 7 章至第 9 章的討論中,點出在新慈善逐漸盛行的年代,土耳其、斯里蘭卡的例子顯示,最弔詭的是原本政府公僕的角色消失了,原本應該健全社會安全網與社會服務供給的功能不見了,「反正有問題,就找這些大慈善家出面解決。」非政府組織在提供跨國福利服務的同時,必須小心謹慎面對所謂「介入處遇」後的非預期效果,以預防將來外援中止或退出服務時,導致社會陷入福利依賴或真空狀態,非政府組織反而抑制了公民社會的成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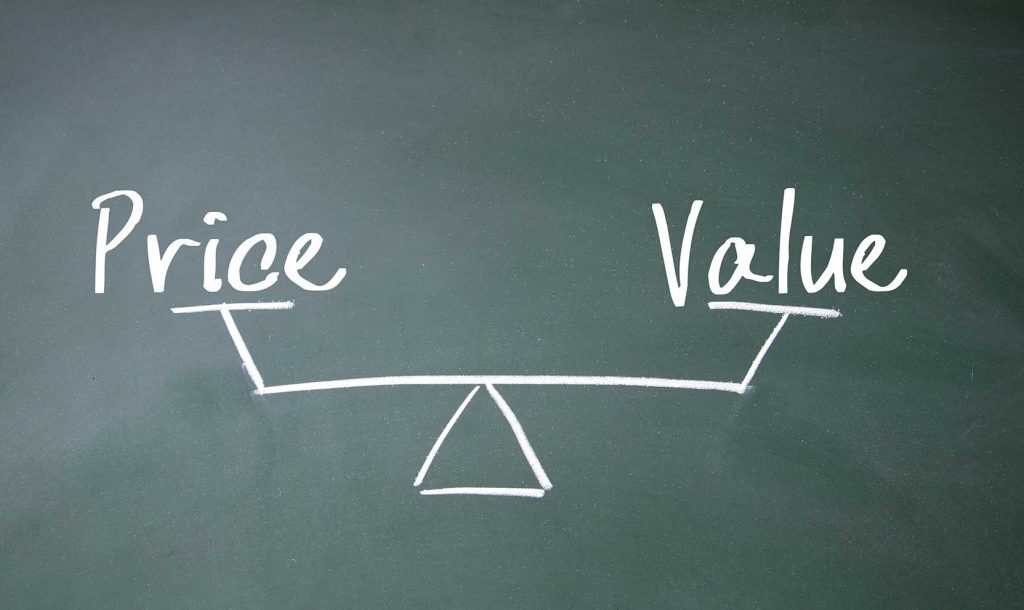
圖片來源/https://goo.gl/2JU6wO
不斷演進的慈善,需要停下來檢討
至於第 10 章與第 11 章的討論,回到英國本身探討政策現況的理論面與數據分析。第 10 章 2 位作者從約翰羅爾斯的正義論切入,強調自由平等原則(liberty principle)與差異原則(different principle)的重要性,應在新慈善發展過程中扮演重要的理論基礎。然而問題來了:理論上所有的非政府組織都應該有促進社會正義的理想,但在英國的討論脈絡中,至少有 10 家受訪機構代表認為,「不見得所有慈善組織都能與社會正義畫上等號。」一個殘酷的現實是,所有組織都宣稱自己促進了社會轉型,但這麼做的背後理由只是為了吸引更多捐款人支持。
第 11 章的作者約翰莫翰(John Mohan)則提醒,當前英國應用大數據分析社會福利的盲點,要小心「慈善沙漠」(charity deserts)效應,意指慈善組織的成立登記地點,未必是實際運作據點,使得明明就有社區有許多貧困者需要更多資源挹注,政府卻誤以為慈善家已經投入夠多資源了,於是直接跳過該鄉鎮社區,錯估社福資源的妥善配置,使得該社區成為社福資源嚴重不足的「慈善沙漠」。意味著單看內政統計數據表面會失準,重點是大數據背後能否如實反映新慈善的真實地域分布。

揭露新慈善利弊,避免寡頭壟斷
對於所有關心當代民主發展的讀者而言,本書的優點在於提供了西方世界的慈善發展脈絡與實務經驗,對於從事國際發展與人道援助的實務工作者或學術研究者而言,學習如何使資本主義與慈善助人與時俱進,可讀性高。然而,本書的侷限在於西方史觀未必能綜觀式的探望「亞洲慈善學」全貌,期待將來有更多東亞本土性研究的開展,這樣的努力需要跨部門集思廣益,從社會學、社會工作、政治學、法律學、經濟學等各種不同面向切入,新慈善才能邁向社會創新。
閱讀完本書後,一個最主要的發現在於促使讀者們重新省視第三部門的民主體質,也許政府在人民高度期待與監督下,已經比想像中開放透明;反而是非營利組織、非政府組織內部責信不公,捐款人指定用途卻不願溝通、董(理)監事會或創辦人的寡頭決策與父權主義、社福組織財源不穩、過度仰賴政府補助,種種志願失靈之現象,使得慈善本身反而變成是「反民主」的來源之一,不但無法促進社會轉型,反而成為孳生社會問題的溫床,值得每一位社會工作者時時刻刻自我警惕。
《新慈善與社會正義:概念辯證與政策論述》(New Philanthropy and Social Justice: Debating the conceptual and policy discourse)
作者: 貝魯茲・莫瓦瑞迪(Behrooz Morvaridi) 編著
出版社:Policy Press
出版年份: 2015(Hardcover, 242 pp.)
索書號(ISBN):97814473169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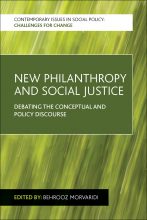
圖片來源/https://goo.gl/PH0b1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