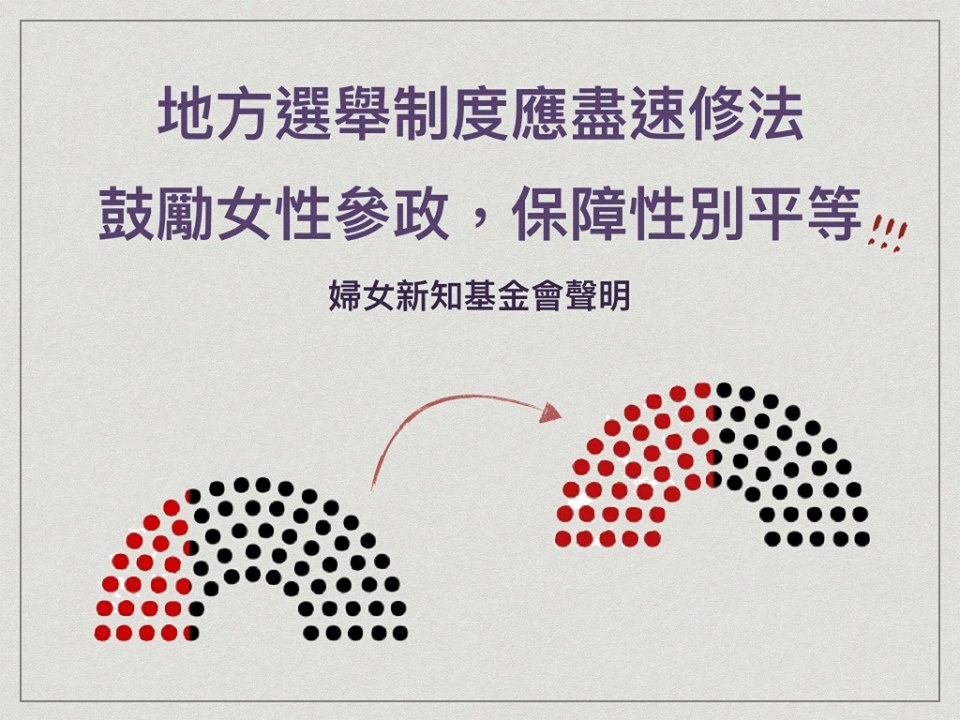花蓮震災中的微光:這一次,我們終於讓救災不一樣
編按:
2 月 6 日過年前的花蓮地震,連長年以來被迫習於震盪的花蓮人都驚恐失色。鎂光燈之餘,眾人討論的是善款的醜聞與疑慮,卻沒想到其中一點溫暖微光曾經綻放。過往,災難中的後勤收容與災民安置,面對高情緒張力的多元專業現場、來自公部門的微妙拉鋸、四面八方不同立場甚至不同黨派挹注的大量資源、地方團體與外來志願動力的衝突……在種種權力角力與曝光競逐中,即使是平日善於與「人」工作的公益服務團體,也沒有自動合作無間的本事。
然而,這次的花蓮不一樣。日積月累的在地網絡連結,在天搖地動的那一瞬間便成為所有災民的後盾。同樣有難解的公權力鬥爭、同樣有服務重疊的團體、同樣有大量的民間資源湧入,這一次,我們卻有了迅速成型的秩序、日程、個管系統、聯繫會議與跨專業的整合。
臺灣在 2018 年的全球氣候風險指數中名列第 7,這個多災多難的小島,就算不提過往未逝的傷痕如 921 或 88 風災,僅 2016 一年間受到的重創,就包括罕見低溫、莫蘭蒂颱風、梅姬颱風、南臺地震與尼伯特風災。然而除了情緒性的大批捐款與物資,長久以來我們鮮少建立起可供依循的工作方法。本篇報導,正在於為這脆弱的小島留下短暫珍貴的記錄。
也許有人會問,這個小小的現場實驗,如果沒有了中間那幾個關鍵的人,沒有了在地願意合作的網絡,還有可能複製到其他救災現場嗎?然而,或許我們該問的是,下一次,我們如何創造這些條件,如何將防災的時間軸拉長,意識到平日裡所有的準備與在地經營,都如同頻繁發生的災難一般,是臺灣人必須慎重以待的集體日常。
2 月 6 日晚上,距離農曆新年還有一週,花蓮市國盛六街與國民八街口一處 2 層樓的透天厝內,東華大學多元文化教育研究所博士生陳乙先正睡在一樓客廳的沙發上,陪伴玩電腦遊戲的母親,父親則在 2 樓的臥房早早就寢,一家安詳。直至深夜 11 點 50 分,一陣劇烈的搖晃衝擊整個花蓮,震央在花蓮近海的午夜地震強度達芮氏規模 6.0,全臺有感。
「我媽媽試圖要走到我這邊來,但她沒有辦法。」驚醒的陳乙先聽見陳母大喊著要陳父儘速下樓,但頂樓陽臺的物品紛紛掉落、移位、堆積住樓梯口,陳父一時半刻無法脫身。待 3 人好不容易聚集在一起,陳家一樓的門已經擠壓變形打不開,還好側邊還有一個電動開關的小門,「好險當時還沒有馬上停電」。陳家 3 口從電動門兔脫,陳乙先身著睡衣,僅來得及在「出門」前,拿上一頂安全帽、手機、錢包。餘震持續著,「一走出來,哇!很像在拍電影啊,天空看起來是一層霧,都是尖叫聲」。
粉塵滿天、陳乙先眼見住家隔壁的白金雙星與吾居吾宿 2 棟大樓以驚人的角度傾斜,才剛用手機攝下 2 張現場圖片,「但我父親要我們快點離開,我們判斷要『逃亡』了」,馬路上的摩托車已經全倒、地面裂開來。「這是 921 之後,我第 2 次因為地震逃出家門。」花蓮地震頻仍,住民早已對時不時的地牛翻身安然處之,難得驚恐。陳乙先指出,這場不再尋常的過年前地震,不只憾動了花蓮人 20 年來面對地震的淡定,也憾動了人心。

圖/billy1125 @ flickr, CC BY 2.0
那一夜,連花蓮人都難安
當晚,陳家 3 人將自家轎車停在住家 1 公里外的花蓮火車站前空地,半寐半醒度過驚恐一夜。隔日早晨 6 點,天空還未全亮,但餘震已停下來,陳家決定回去拿一些緊急離家前尚未取出的證件。驅車反往住家前進,放眼所及都是路倒的物品,無處停車,「我們想到中華國小嘗試尋找空地,結果看到已經設置收容中心,我們就進去了」。
離白金雙星與吾居吾宿 2 棟傾斜的大樓及陳家等受損民宅距離約 400 公尺處,便是花蓮縣政府於 2 月 7 日凌晨開放為收容中心的花蓮市中華國小。花蓮縣府在地震發生後同時成立花蓮縣立體育場與中華國小 2 處收容中心,相距約 4 公里。中華國小因鄰近主要受災民宅區,清晨起便開始有政府、民間援助單位陸續進駐學校內大禮堂,鄰近災民也許是聽到口耳相傳的訊息,也許是不知該去何處避難而只是路過,也慢慢都聚集到中華國小。
首批動員起來進駐中華國小收容中心的世界展望會社工督導江文琪大約在中午時分抵達,「當時禮堂內還是很混亂,沒有統一的窗口,援助人員與災民來來去去。」世界展望會內部有應變緊急災難的兒童關懷中心(Child Friendly Space,CFS)定期演習與設點機制,在第一時間便決定在 2 處收容中心啟動 CFS,讓社工進場,陪玩、聚集並安撫孩童,也減輕家長焦慮。江文琪表示,到達中華國小後,「看到的災民其實都是附近的住戶,因餘震頻繁不敢回家,每個人壓力都很大。」
陳乙先已經在禮堂待上一會了,她解釋現場空氣中的浮動不安:「我們都在想,過幾天就要過年了,接下來怎麼辦?」一夜過去,餘震不斷,在中華國小內聚集了一夕之間不能或不敢回家的花蓮人,大部分的人都不是重傷,但身體仍感到緊繃疼痛或是心理難解恐慌焦慮,家雖近在咫尺,但接下來怎麼辦?
花蓮縣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成立已經快 1 年,工會成員是來自花蓮各個社福組織、學校、醫院的專業社工。地震發生當晚,現職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原住民社會工作學程)助理教授,同時也是花蓮社工工會發起人兼理事的黃盈豪,率先在工會群組內確認有無夥伴受困受傷,隨即腦中警鈴大作:「明天開始就要做很多事了。」

東華大學民族事務與發展學系(原住民社會工作學程)助理教授、花蓮社工工會發起人兼理事的黃盈豪。圖/NPOst
權力系統展開,如何讓「關懷」不重疊
黃盈豪曾有 921、汶川地震與莫拉克 88 風災等救災經驗,對災難應變與救援並不陌生,「馬上就要動員救災」是他第一時間的判斷。2 月 7 日中午,他帶著咖啡去中華國小探班已經開始值班的世展社工,同時也是社工工會夥伴的江文琪,看到現場已經來了若干社福組織、醫療團隊、花蓮縣政府社會處、衛生局與花蓮市公所社會及勞工課的承辦人員,但現場人來人往、各做各的,「好像沒有個統籌」。
現場統籌的單位應該是誰?當日下午約莫 2 點,花蓮縣政府決定分流管理,移交中華國小的收容中心給花蓮市公所負責,而縣政府人員則撤出,專門處理體育館的收容中心。花蓮市公所社會及勞工課課員詹志榮指出,在這次中華國小的收容中心運作中,市公所社會課負責的是災民收容與登記,以及在收容所中的生活所需,市公所固定有 3 個承辦人員在現場每天輪班,並協調其他公所人員機動支援。
黃盈豪與花蓮縣衛生局的人在縣府撤出之前,一起架設起了「安心關懷站」的布條,準備服務身心緊繃的災民,但隨即發現縣府要準備撤出,移交指揮權給市公所,而市公所的人力明顯不足,卻已經有若干社福、醫事、宗教等不同民間組織進駐服務。災民的空間、不同組織的空間、政府部門的空間任意的在中華國小內,隨著先來後到而無邏輯的占地分隔,物資也紛紛湧入,對於建立秩序的需求急迫性越來越高。

圖/黃盈豪提供
黃盈豪因認識縣府衛生局承辦與花蓮市公所承辦社工,且身兼教職與社工工會幹部等獨立於個別組織或公部門的職業特性,熟識社工間的人際網絡與過去救災經驗豐富,在現場隱然成為有能量與不同團體協力合作的中心人物。黃盈豪當下也意識到未來一個月可能都得留在收容中心協助,「現場做的服務策略,就是用安心關懷站作為平臺,協調每個組織都可以此為溝通據點」。
這個搭建平臺的策略看似合乎邏輯常理,實務上卻不簡單。黃盈豪指出,過去救災經驗的日常,通常是「組織想要做什麼就做什麼」,最令人憂心的通常不只是災民,還有不同組織之間的權力角力,當每個團體都有自己的牌子要掛要拍照,如何讓大家都能安心分工,或是說白了,願意把「理論上」屬於自己的業務內容「切割」給其他組織進行也許可能更好的服務,成為最大考驗。
「過去救災的經驗發現,很多問題都是橫向的聯繫做不好。」詹志榮也提及,過去的救災服務常常會有相同功能的不同組織同時在現場,每個組織各自獨立與分頭行動,以「強調自己有在做服務」。但「同一個災民每個組織都要去問一遍情況,問到第 3 遍災民就要變臉了。」時有災難服務成為組織插旗、畫地盤、爭曝光、爭案量 KPI 數字的情形,對於民眾卻成為騷擾,「怎麼樣讓每個組織做不一樣的事情,不要重複」,成為挑戰災難現場的大難題。

圖/黃盈豪提供
所有人都需要秩序:訂定日程、聯繫會報、建立個管系統
詹志榮坦承,對公務機關而言,照顧災民的首要就是不可以再有「出人命」這樣的大事,第 2 條是讓災民吃飽睡好,但「亂通常是一定會亂」。而此次公部門人力明顯不足,在責任劃分上,市公所承擔起災民收容後的物資調度、禮堂外的秩序維持、交通動線等工作;動員最多志工、也最快到場的慈濟慈善基金會則維繫了場內外幾乎所有的總務事項:消毒、清潔、打掃、熱食、保暖衣物等後勤協助,並啟動劃分飲食、就寢、活動等不同空間。而對內的災民需求與評估,則由民間各個專業社福團體逐漸掌握,無心插柳的形成一種新的災難應變文化──
每天定時在下午 5 點 30 分舉行「聯繫會報」,邀請在場社福組織進入,進行公私協力、跨專業對話溝通,並分工協調。這也成為中華國小這 7 天救災工作的主節奏。
「一個救災現場就是要有救災體系,如果都沒看到就是要自己來。」花蓮縣臨床心理師公會監事陳百越,是第一波到達中華國小的心理師,也是第一個明確意識到,必須要求現場公部門主責者拿起麥克風向民眾佈達,包括收容中心的日常作息會是什麼,並且透過民間組織協力建立系統,以準確掌握災民狀態,創造讓災民與組織可以共同合作的雙軌機制。
幾點會有活動操、幾點會有組織帶領祝福活動、隔日的行程又會有什麼,看似是每日的小事,卻是災後安置現場重要的心理安撫。陳百越指出,震災過後,受傷的民眾都在醫院,會選擇留在中華國小收容中心的大部分民眾,雖然身體沒有重傷,但「有的嚇到連家人名字都說不出來、有的沒辦法睡覺、有的拖著小孩」。與體育館收容大部分來自外地的遊客不同,中華國小留下來的都是「想要離家(災區)近,又不敢回家」的花蓮住民,對於日後生活恢復有極大的疑慮、都有災後的心理狀態評估與社會資源挹注需求,也因此,「讓民眾掌握幾點鐘可以做什麼」,是建立秩序的第一步。

每天定時在下午 5 點 30 分舉行「聯繫會報」。圖/黃盈豪提供
秩序建立後,接著就是現場的團體協調。從 2 月 7 日開始,下午 5 點半由市公所主導的聯繫會報,是每一天的重頭戲。黃盈豪與陳百越相識於聯繫會報中,當下便建立未來可以合作的團隊模式:由花蓮社工工會、花蓮家扶中心、花蓮諮商心理師公會、花蓮臨床心理師公會等 4 個民間單位(後來又加入花蓮職能治療師公會和東區醫療網等團體),一個組織每日各派出 2 名社工、心理師或諮商師,共 8 個人分別進入災民中地毯式訪視,取得基本個人資料、建立個管系統,每天並與市公所核對出入名單與生心理及社會需求,篩定需要加強撫慰與跟進的個案。
「每一個災民都有一個專屬的資料夾。」黃盈豪強調,從收容第 1 天就透過社福專業人員將災民資料蒐集建檔、建立個管系統,並交由學生志工後續建立電子檔。這個初步建檔與初篩的流程,令每個現場的志願工作者不論第幾天到達現場,都可以後續跟進而減少詢問同樣的問題、對災民造成不必要的干擾。隨著災民身心狀況與需求不同,黃盈豪與陳百越也會在聯繫會議上協調溝通,讓不同專業與特質的社福、心理人員跟案確認。於是,災民可能會在不同時間點受到社工、心理師、諮商師或職能治療師的服務,讓情緒、社會資源、身體等因災變而起的種種不適,受到專業的撫慰與調整。
此外,現場來支援的社工工會專業人員多半都是以志願性質參與,這些來自不同組織的在地社工,往往一望即知災民中有哪些是需要特別關懷的脆弱家庭,這些在地連結與民間團體對於現場家戶的熟悉和即時進場,成為讓災民得到安全照顧的一把鑰匙。
日積月累的在地網絡與社會關係,成為收容服務根基
「這個體系是動態的,」黃盈豪強調,由於災民、組織、工會、師公會等不同群體間的非正式關係建立並非始於救災,而是過去生活的累積,以及緊密的花蓮人際網絡,因此災難就像更進一步的檢視,讓大家聚在一起時,能夠「看到不同的團體非常清晰的各自樣貌。」每一種專業的價值都很不同、每個人的個性也不一樣,黃盈豪自認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串聯跨專業的合作與統籌:「我每天都在問,自己是不是可以真心合作的人。」
花蓮家扶中心社工督導王芯婷也是社工工會成員,雖然家扶中心與世界展望會都以服務兒童作為組織主要業務,但此次中華國小內的業務分工,近似安親班功能的兒童關懷中心(CFS)是由世展社工全面投入服務,家扶中心的社工則負責下場訪視,並與心理師合作,透過畫圖與遊戲媒材初評孩童的心理創傷程度。

圖/Kelly Sikkema @ Unsplash
「除去組織本身,其實我們社工之間彼此是認識的。」王芯婷強調,透過社工之間彼此對專業的掌握與熟識的默契,同一個個案通常不同組織會有不同的資源協助,跨組織的合作在收容中心內由此逐漸自成一個正循環的體系,「不用搶工作也不去推工作,同時還避免重疊服務」,這對過往在許多服務現場總是各憑本事較勁的各團體而言,幾乎每個人都異口同聲表示是「第一次」:「這一次,大家都只想著怎麼把事做好。」
「工會中有救災經驗的只有盈豪,我們其他每個人就像在扮演『支援前線』。」花蓮社工工會理事長,同時也是花蓮門諾基金會社工林盈杉指出,社工工會成員雖然大部分不是花蓮人就是長住花蓮的新移民,但對於地震、救災多半沒有概念。黃盈豪在工會群組中不斷提出小到影印、大到在工會粉絲團徵求排班社工等訊息,這些動作都因工會已經跨組織的運作起來而能得到響應。「我們也在每天的粉專貼文中,傳遞並告知現場訊息」,由此也安撫其他不在安置現場但同樣關心的民眾。
地震震出來的,都是長久存在的問題
中華國小收容中心的服務,在收容後第 6 天的晚上,由縣府人員宣布將在第 8 天上午,也就是除夕前一天(2 月 14 日)結束安置,不論是對於社福人員或是災民而言,離撤站只有一個整天的準備日。本來心理準備好要在收容中心過年、甚至長期抗戰 1 個月,開始設計後續服務方案的社福工作人員,當下緊急收到要撤離的指令,並且對於現場個案未來的處遇與追蹤,至今沒有一個組織清楚。
在情人節要各自回到工作崗位,與共渡救災的工作伙伴與災民「分手」,對於大部分志願投入現場服務的社福人員猝不及防。不過,此次中華國小的救災合作經驗,跨專業與組織間的競合達到如此非預期的「順利」,其實對這些社福工作者來說,同樣讓人意外。
有多次救災經驗的黃盈豪直言,過去許多救災現場就像是園遊會,你插你的旗子,我發我的傳單,你找馬戲團來撫慰災民,我就能找更吸睛的表演,「怎麼把不同專業的團體放在一起運作、怎麼定義災難、怎麼讓災民擁有主體性,以及怎麼召喚公民社會的對話」,這些都尚未在臺灣的救災場域中,磨出標準規程。
救災現場的「成功」模式也許沒有固定的版本,但在中華國小的經驗中,「其實就是玩一個小模型給政府看」。陳百越建議,未來公部門針對救災,也許可以事前規畫與培訓團隊,而那個可以建立系統與現場派案的工作人員,必須具備了解各個專業、職類並妥善與不同團體溝通的能力。

面對安心服務站即將撤站之際,受過協助的民眾紛紛留下祝福小卡。圖/花蓮縣社會工作人員職業工會 fb
在中華國小收容中心的 7 天 7 夜,似乎透過一個願意協調的公部門、幾個在救災現場受到組織信任的關鍵人物、一批志願到現場且專業自制的社工、心理師、志工、學生,在土法煉鋼的自製個案管理系統下,撐出了跨公私、跨專業、跨組織互相合作與對話的機制和空間,「就像是救災現場的烏托邦。」江文琪說。返回職場 1 個月後,許多在中華國小收容中心協力過的工作人員,都異口同聲的形容那恍如「做夢般」,雖偶有專業對峙張力,卻合作順暢的一週。「有輕微的權力拉扯,但跨專業合作與相互間願意配合,讓我們的精神很活躍。」王芯婷重申。
然而,這樣的協力模式可否在下一次臺灣的災難現場得到應用與驗證?災難這面鏡子可以照出多少人性動機的複雜,又能映証多少人與土地的韌性?花蓮災情結束 2 個月,媒體的鎂光燈漸消,公部門、社福團體與災民之間的繫帶要如何扣好扣緊,捐款如何善用在對的事情與方案上,災民的定義與後續追蹤關懷如何落實,一切都還未解。「地震震出來的,通常都是長久存在的問題。」黃盈豪說,過去的南投與屏東政府在災後都與民間單位有進一步的合作,形成當地公民社會實質的變化,而花蓮縣政府未來所釋出的合作模式與機會會是什麼,所有人都在關心。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