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與惡的距離》拔除標籤後,社會對精神醫療是否還有扭曲的期待?
臺灣曾發生精障者傷害孩童的悲慘社會事件,內湖擄童案發生之時,筆者曾向醫師李彥鋒請益。李彥鋒服務於嫌犯強制就醫的院所,當時這位年輕的精神科醫師,對於此一重大社會案件並不迴避,讓筆者問出藏在心中已久的疑問——為何這些存在精神症狀的加害人,大多傷害小孩?

圖/黨一馨提供
家庭因素,是否容易造成思覺失調症發病?
李彥鋒說:「這很簡單,他們今天如果攻擊成人,大概會被還擊,他們(精障者)的動作反應比較慢。」
這個邏輯易解、簡單,但要被輿論鋪陳出來、推上公共討論卻很難。險些遭害的路人、稚幼生命的喪失,讓精障者議題淹沒在死刑存續議題的討論中、以牙還牙的快慰裡,談論「精障」甚或「思覺失調症」,如果沒有一條適合的路徑,徒增標籤,又太沉重。
所幸,臺灣的戲劇工作者默默貢獻心力,《我》劇大方探討精障者標籤,再輕悄將它撕去。編劇引導閱聽者進入由林哲熹飾演的「應思聰」發病的深刻脈絡,從職業生涯的不順開啟擦槍走火切入。巧合的是,思聰險些傷害的對象,也就是幼兒園的小朋友;他挾持的,是稍微與他勢均力敵的人。
究竟,精障者發病的時機,和壓迫的環境有否關聯?基因與生物因素,能因為友善的環境而不使患者發病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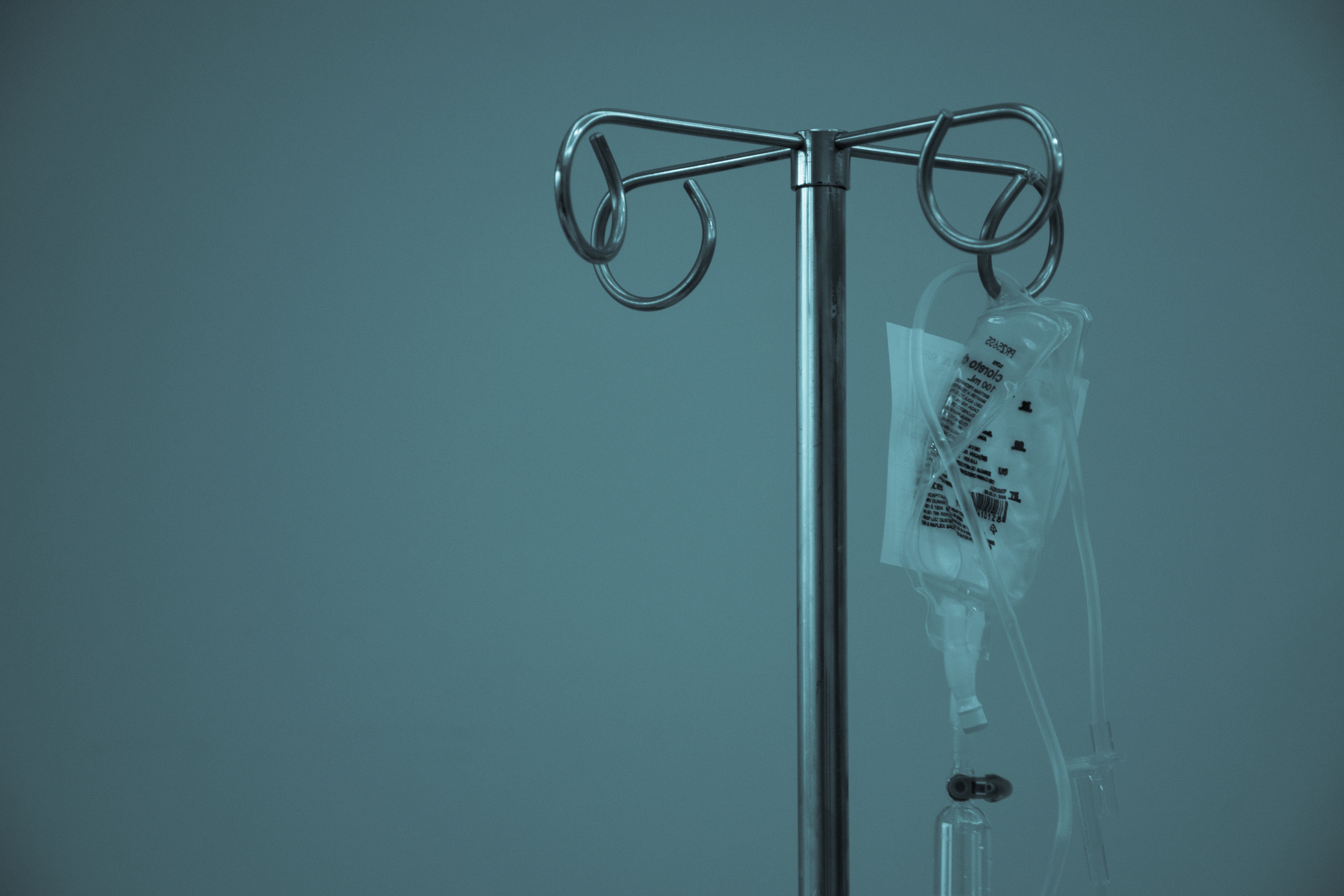
圖/Marcelo Leal @ unsplash
李彥鋒說:「發不發病這件事情,到現在沒有一個人說得準,當然,遺傳一定有關係。爸爸媽媽如果都是(精障者),你有 1/3 的機會是,但是也才 1/3;即便你的同卵雙胞胎,他是,你也只有一半的機會是。所以,基因有沒有影響?有。但是它是不是百分之百,不是。」
李彥鋒表示,基因當然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接下來就是環境,「他的成長過程中,是不是遭受到什麼壓力?若他沒有辦法去負擔這個壓力,當然有機會發病。但是,遇到什麼一定會觸發思覺失調症的事情,也並非如此。發病的原因太多元了,現在的研究也沒有辦法說,什麼原因一定會造成這個疾病。」
越早發現,越有機會減緩身、心功能退化
李彥鋒強調,思覺失調症並不是昨天沒有、今天就發生的疾病,「它是慢慢、慢慢的過程,有些人可能本來就有一點點病徵,可是還沒發病到需要就醫。舉例來說,當病患確診的歲數是 20 歲,可能在 14、16 歲的時候,他的功能就有慢慢退化的狀況,例如在學校生活講話沒有邏輯,注意力變不好、睡覺也睡不好⋯⋯。他的功能退化到一個程度之後,家人終於帶他去就醫了,細問之下才知道他有幻聽,怪不得他在學校的時候有時候會自言自語。這些症狀慢慢出來,可是那時候還沒有發病。」

圖/Hush Naidoo@ unsplash
如果這些症狀沒有被發現,是否延誤就醫時機?對此,李彥鋒說:「的確,越早發現,越有機會減緩它繼續變壞的變化。」
孤立,經常讓患者的狀況越來越糟
《我》劇中,應思聰有被母親拋棄的情結,腦中會出現家庭成員負面的耳語。家庭動力是否容易造成思覺失調症更容易發病?對此,李彥鋒認為這很難下結論,他只能從處遇的後端看到,「我們遇到大多數情況嚴重的病人,家裡給的支持都不太好,冷落也有、口頭暴力也有。有些患者生病久了,發病的時候可能會有些激動的情緒,家人不想要跟他住,沒有人想要理他。後來,家人可能給他一個房子讓他自己去住,說:『你就自理,就不要跟我們有往來』。」
這種孤立的狀況,經常讓患者的狀況越來越糟,「你說他一個人,他會按照時間吃藥嗎?」李彥鋒說。
為釐清大眾理解,精障者在精神醫療急性病房受到的照顧,是否就是被綑綁、打針?李彥鋒解釋:「保護約束,聽起來好像不人道,聽起來好像是處罰,好像是在剝奪他的一些自由跟權利,可是我們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

圖/rawpixel @ unsplash
「在可能傷害自己、傷害別人的考量之下,我們必須讓他先鎮定下來。在這過程當中,要用打針的方式,讓他的情緒鎮定下來。病人打針到藥效發揮,搞不好要 20 分鐘到 30 分鐘,這段時間沒有辦法放著他跑來跳去。在他們情緒沒有辦法控制的情況之下,其實是危險的,所以,保護約束其實是在保護他。」
李彥鋒:病患認定的「幫」可能和醫師不同
應思聰因探望爸爸,得以暫時離開精神醫療病房,他對姊姊思悅說:「在外面的感覺,比較像人。」聽在精神科醫師耳中,又是什麼感覺?
對此,李彥鋒說:「精神醫療院所是一個封閉的空間,它暫時沒有自由、自由是被剝奪的,可是,精神科病人也不像內外科病人,知道『我生病了,我需要住院,然後我也同意我來住院。』」
說到這裡,李彥鋒給予《我》劇高度讚賞,「我覺得這齣戲演得非常好的是,它把此疾病演得很真實,這就是非常典型的狀況。大多數病人的第一次發病,都是類似這個狀況。」
「他(應思聰)是得過獎的導演,但是已經無法產出作品;他幾乎都在家,沒有什麼人際互動,社交功能也下降;他整體生理、心理功能是退化的;他在夏天的時候,戴毛帽、穿毛衣,他的穿著不合時宜⋯⋯這些都是劇組非常細微描述出來的細節。」

圖/Jeremy Yap@ unsplash
李彥鋒進而表示,《我》劇播畢前,他每週日晚上定時收看,「我們每個人看東西的角度不一樣,劇組用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不同的家庭去描述一件事情的時候,會有不同的情緒出來。可是不管你在哪一方,我們是不是都做錯了一些事情,所以才叫,我們與惡的距離。」
他生動地描述起自己行醫中的震撼體會,「有一個妹妹來看診,她說,妳可不可以幫我,她的意思就是幫她自殺,這句話我後來想了很久⋯⋯。」
李彥鋒說:「我們認定的幫,跟病患個人認定的幫、跟家屬認定的幫,我覺得完全不一樣。思覺失調症患者想要我們『幫』的,是你幫我離開醫院,我不想住院、我不想吃藥,你讓我出去自由好不好;對家人來說,想要我們『幫』的,是我的孩子已經失控了;而我們醫生認為的『幫』,是把藥送到病患的嘴巴裡。醫生有時候會自以為我們在幫病患,但是殊不知,他需要的幫忙可能是別種。」
精神科醫師眼中的社工
《我》劇中的社工師宋喬平有亮眼戲份,她給的專業,和精神科醫師又有何不同?現實生活中,精神科醫師眼中的社工角色又是什麼?

圖/Harry Tang@ unsplash
李彥鋒表示:「醫生沒辦法為了一個案,花這麼多時間、打這麼多電話,追蹤訪問家屬那麼多次,去一個一個了解。」李彥鋒強調,社工做的家庭評估很重要,「社工協助我們跟對病患、病患家人建立一個比較完整的溝通,最重要是出院以後,你要瞭解這個病人回家以後,每天要吃的藥,有沒有家人能協助他?」
對照自己的職業角色,李彥鋒回憶劇中印象最深刻的畫面——王赦律師上政論性節目,討論精神患者需不需要被強制就醫,與精神科醫師林一駿激盪出論辯火花。
這讓李彥鋒聯想到自己身為精神科醫師的日常,「當有小朋友被挾持,擔心的爸媽、焦慮的民眾,當然希望犯人無論如何都要被關起來,但人權律師或是患者本人,會覺得你為什麼剝奪我的自由?」
強制就醫解決得了社會問題嗎?

圖/Jair Lázaro@ unsplash
李彥鋒解釋,強制就醫這件事情是由〈精神衛生法〉規定,經由申請委員會判定需不需要強制住院,至於認定有否自傷傷人之虞,通常由在場精神科醫師做判斷,「法律上訂得蠻寬鬆的,你不是有自傷傷人行為才需要被強制住院,你有自傷傷人之虞,意即『我覺得你有可能、有機會』就需要被強制住院,認定的責任在醫生的身上。」
〈精神衛生法〉規定一次住院的上限就是 60 天,「如果狀況還是不穩定,有自傷傷人之虞,得再延長一次,也是以 60 天為限,總共就是 120 天。」李彥鋒說。
思覺失調症的治療關鍵,就在調節他腦內的多巴胺,「所以確定他把藥服下去,這在住院期間做得到,出院後便很難,假若他隻身一個人,或他的家人在其他縣市,誰盯他吃藥?」
對於這樣曾有自傷傷人之虞的病患,出院後豈不讓院方也捏把冷汗?李彥鋒說:「對,捏把冷汗,所以他出院前,我們會打長效針,至少他未來一個月,血中的藥的濃度都還是維持在一定的水平。」
那麼,一個月後呢?

圖/Joshua Earle@ unsplash
李彥鋒解釋,〈精神衛生法〉當中有「強制社區治療」,假若患者住在一個固定的地方,「我們還做得到去他們家拜訪、幫他打個針、幫他送藥,這些努力我們都會做,前提是找得到他,可是萬一這個病人居無定所⋯⋯。」
這樣的限制與額度,解決得了社會問題嗎?社會是否對精神醫療有扭曲的期待?
最終,李彥鋒表示:「不是每個精神病人一定會越來越壞,思覺失調症的患者 1/3 後來好了;1/3 維持現狀;1/3 越來越差。當然,我們希望到手上患者,可以有機會康復,如果沒有辦法康復,至少維持現在的功能不要變壞;萬一真的變壞了,我們希望病患變壞的速度再減慢一點。」
他試圖讓精神病人及其家屬看見一個治療的願景,或者就像劇中的精神科醫師,不是完美,卻絕對真實。
筆者問他看《我》劇有沒有哭,李彥鋒回答:「我覺得不是被打動,這個戲太真實了,這就是我每天都遇到的事情啊,真實到有點起雞皮疙瘩⋯⋯。」
採訪後記:
我過去曾為精障領域的社工,採訪李彥鋒的過程中,我想知道究竟精障者發病的契機和其受壓迫的處境有否關聯;基因與生物的發病因素,是否能夠因為友善的環境而不迸發?
有這個疑問是因為,我有一位親近的家人也是精障者,她發病於 30 餘年前的台灣社會,發病場域在於一個不友善的職場,在那大家都說台語,「外省仔」的她聽不懂,她開始告訴家人,有人要傷害她。
我在精障領域服務時,遇到了一位和我家人處境甚為雷同的個案,她清晰地描述她在職場遭遇的排擠,及當時工作帶給她的擠壓,她亦在職業生涯的斷裂處發病。
是不是聽起來都有點熟悉?就像《我》劇中的應思聰。那麼,精神科醫師會怎麼看?
李彥鋒表示:「我覺得很難去推測、確定說,有特定原因造成發病。精神病它不是短期之內的症狀,這個疾病是你腦中多巴胺已經出現一些異常,它會有一個臨界點,它會有一個高點,突破後才會有嚴重的症狀足以讓人辨識出來。」
「所以,有可能這個病人還沒發病,可是他已經有前驅症狀(prodrome),在功能退化的情況之下,又還沒達到手冊開的那幾個條件,這樣的情況是有的。」
精障者發病的契機和受壓迫的處境有否關聯;基因與生物因素能夠因為和緩的環境而不迸發嗎?雖然我迄今沒有獲得解答,但,如果它的答案是肯定的,那我們對於精障族群,還有很多面向可以努力,還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看《我》劇時,我也很少哭,因為太真實。應思聰背負著精障者的標籤,但他又是那麼真實的關心著爸爸,探望住院父親時,以僵滯動作緊握父親的手,說:「要好。」還有保護大芝的真性情,都讓人如此動容。就如同我的患病家人,他們有時讓我不解,卻也帶給我很多溫暖。
延伸閱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