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民為什麼支持戰爭?關於同理心的黑暗面
翻譯/劉晏汝
大多數人都同意能理解他人的感受是善良的要件,如果我們能站在他人立場思考,多替他人想一點,那我們就能更了解他們的喜樂與痛苦,是吧?
事實也許沒那麼簡單。
雖然人會因為有同理心(empathy)而幫助別人,但同理心也會掏空我們的情感,或引起想報復的心態,更重要的是,同理心可能混淆我們的判斷力。
大部分人討論到同理心的道德意義時,通常只聚焦在它的情緒面。歐巴馬成為美國總統前,在一段演說中強調同理心的重要──
透過他人的視角看這個世界,無論是飢餓的孩童、遭資遣的煉鋼工人,或因為風暴來襲而頓失家園的家庭,一旦選擇擴大你關心的範圍,無論是最親密的朋友或毫不相關的陌生人,你都能感同身受,那麼你就無法不採取行動、不出手相助。
歐巴馬最後一段說得沒錯,且目前有相當可觀的研究能支持心理學家巴特森(Daniel Batson)所謂的「同理利他假設」,這個假設指出「對他人有同理心,會讓你更想要幫助他們。一般來說,同理心能幫助打破人與人之間的藩籬,它和自私冷漠背道而馳。」

過多的同理讓情緒失控
然而,同理心是很複雜的情緒,如果時常出現同理心,會導致你情緒疲勞。巴龍柯恩(Baron-Cohen)在他 2011 年出版的《邪惡的科學》中引用心理學和神經科學等研究,指稱邪惡的概念應該理解為「同理心的消蝕」。他假定每個人會依照「同理心曲線」出現不同的傾向,此曲線從等級六的「隨時關注他人的感受」,到等級零的「毫無同理心」。
人們若處在等級六的狀態下,會用情緒性同理心面對問題,對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這會導致心理學家所說的「擬情困擾」(empathetic distress),這些人會出現超出同情、關心或幫助他們所愛的渴望,來映照出他人的苦痛。最終,他們的情緒會出現極大的動盪,端視他們遇到什麼樣的人,長遠下來會對個人帶來毀滅性的傷害。
同情(compassion)和真正的同理(empathy),其差異在一系列測試中得到科學佐證,根據牛津《社會認知與情感神經科學》學報顯示,大腦對於同理和同情的感覺會有不同的反應。研究員將受測者分成兩組,一組接受同理訓練,受測者會專注在感受他人痛苦的能力;另一組則接受同情訓練,受測者會對於苦痛產生溫暖、關懷的反應。訓練員讓兩組人觀看關於人類苦痛的影片,發現同理訓練組的大腦中,對疼痛感受產生同理的區塊會變得更活躍,負面影響也會提升;相反的,同情訓練組卻能抑制負面影響,且有較多受測者產生正面影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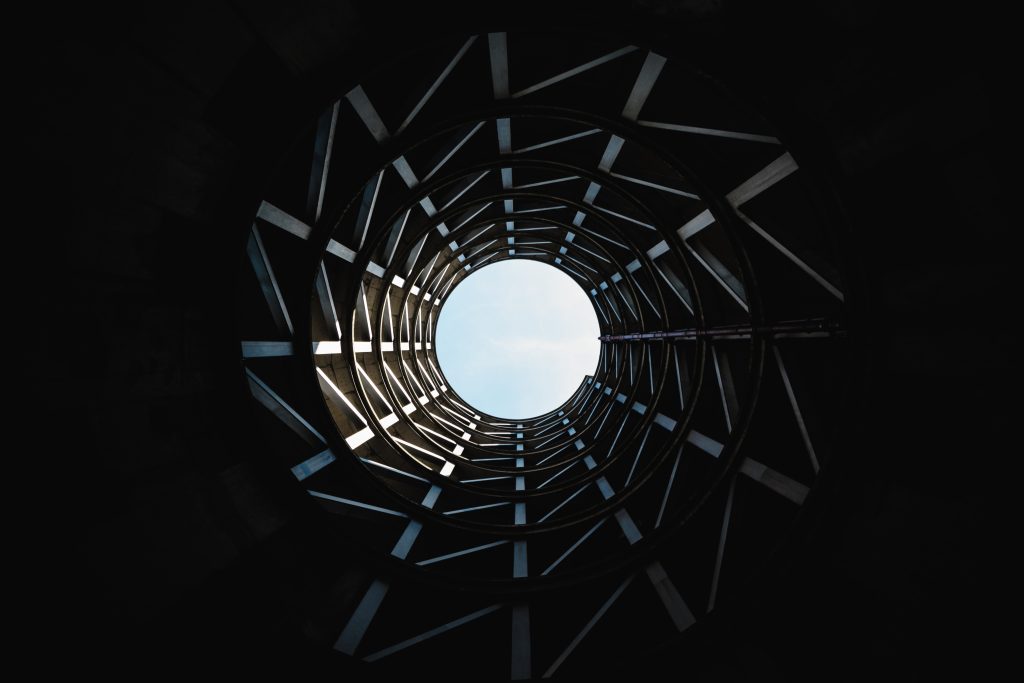
這項發現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為它代表擬情困擾並非人們採取行動的要素,有同情心的人也可能重視其他人的性命,也能理解飢荒造成的不幸,也可能因此捐款做慈善。
被巴龍柯恩列為毫無同理心、等級零的另一個極端,我們通常將他們視為精神病患、反社會人士,或心理變態、反社會人格者,但較具侵略性的人真的比較沒有同理心嗎?根據研究資料與報告顯示,只有 1% 的研究對象是因為缺乏同理心才出現侵略性的行為,這代表缺乏同理心並不是形成侵略性行為的要素。
同理心與侵略性行為
相反的,同理心也許反而會導致侵略性的行為。生氣和同理心有許多共通點:兩者都在年幼時期顯現、存在於人類文化中,且兩者都和社會有關。生氣通常是在遇見可感知的不平等、殘酷或不道德後產生的反應。許多目睹犯罪或不公不義的人都會感到同情,出現關愛和同理心,但對象不是犯罪者,而是受害者,因此可能導致我們替受害者討回公道或報復犯罪者。

心理學家布芬(Anneke Buffone)與普蘭(Michael Poulin)則致力於找出讓人們對升壓素、催產素和賀爾蒙特別敏感的特定基因,這些激素與同情、互助和同理心有關。不出所料,擁有這些基因的受測者,其同理心和侵略性的行為關聯很高,天生比較有同理心的人如果看到陌生人受苦受難,會出現更侵略性的行為。
因此,雖然大多人都認為同理心肯定利大於弊,不需嚴加驗證,但太有同理心的人可能會精神耗弱,也會讓想要保護無辜者和報復罪犯的人產生侵略性的行為。
同理心影響判斷,重個體勝過群體
此外,同理心也是有偏好的。人們對於有魅力的人、和自己相似的人,或具有同樣種族或國家背景的人,會產生更多同理心。布朗(Brown)和他同事在 2006 年發現,人們在觀看一系列面孔的照片時,會對與自己同樣種族的面孔產生較多同理心。史都默(Stürmer)等人則在 2005 年發現,唯有在同一族群的人急需幫助時,同理心才會驅使人們伸出援手。
也因此,同理心是狹隘的。同理心能讓我們連結到特定的個體,同時卻對統計數據無感。這也是傳播專家都會藉重特定個體的生命故事來宣傳的原因之一。如同部落客伊凡斯(David Evans)所說,把統計數據和「人名、歷史和抱負」做連結,是確保眾人參與和取得資源、進而推動目標的要件。研究顯示,我們對一個個體愈了解,對個人的關心愈會勝過群體。

這一點,政治人物倒是濫用得游刃有餘。他們會在大選中,拿駭人的個人苦難故事來創造一個議題,學者稱之為「恐懼政治」,因為這些個人故事會引起我們對無辜受害者的情感,促使我們支持用嚴苛的法令對付罪犯,這種反應甚至會混淆視聽,讓我們轉而支持戰爭。政治人物能生動描述戰爭的好處,例如替受害者報仇等,相較之下,戰爭的代價卻只會被化為抽象的統計數字。
如果我們暫時放下同理心的黑暗、極端面,大眾論述也許能更公平、更符合道德。如果我們能真正體會,失去一百條性命比失去一條命更加嚴重,如果我們能認同,遠在他國、和我們看起來截然不同的人,他們的性命跟我們的家人一樣重要,那麼政策就能有所改善。我們或許也能更理解違反人權等議題的重要性,因為這些議題都需要理性的回應才能受到重視,我們也能重新思考人道援助和國家的司法正義體制,選擇合理的道德義務、承擔可能的後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