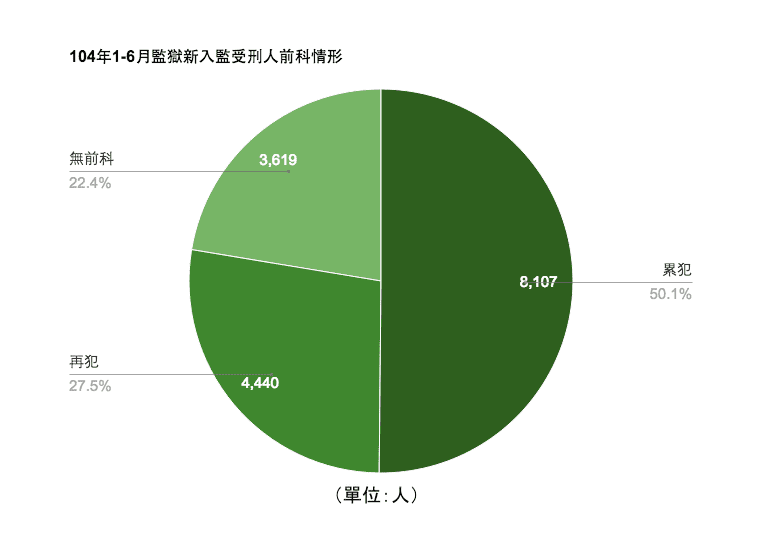讓監獄裡的受刑人擁有自尊;讓社會擁有安全感-專訪監所關注小組陳惠敏
在台灣,要談受刑人在監獄中的人權似乎過於遙不可及。「為何要費心照顧做錯事、本應接受懲罰的人?」是大眾最直覺的反應。本次專訪監所關注小組,積極推動監所改革的陳惠敏說:「把監所搞好,是替社會增加安全感。」
如果我們認為把犯錯的人關起來、剝奪其自由仍然不夠、必須承受在獄中惡劣的對待,那麼我們剝奪的可能已經不只是受刑人的「人權」、更是能夠幫助他們回復到社會中正常生活的「人格」;如果我們讓受刑人在獄中必須學習靠幫靠派的生存之道、而非學習如何和常人良好溝通並且正確抒發情緒,我們如何期待他們出獄之後能夠和社會正常互動?
而當我們稍加關注北歐國家的「開明」監所政策時,再度感到台灣的監所,真的太少、太少人關注了,加上監所本身不透明的特質,讓人很難輕易掌握這個議題的盡頭何在。這次的專訪,會是想關注監所議題的人一篇很好入門的文章,也開始思考-「那些被關在監獄裡的人,真的和我們是『兩種人』嗎?」
監所存在的終極意義,應該是消滅監所本身
談到監所改革,我們第一個會想到的是北歐的典範。其實,在北歐採取開放性的監所政策之前,也經歷過一段高壓導向的時期,直到專家和社會發現再犯率依舊居高不下,才開始展開改革。
「無論是監所關注小組、還是現在官方的矯正署,其實目標都在於『降低犯罪率』,但我們認為若要這麼做,監所應該要把更多焦點放在『協助』受刑人,改變他們出獄後的生活,才能談『降低犯罪率』。監所存在的終極意義,應該是消滅監所本身。」陳惠敏表示。
保持和外界聯繫,是受刑人「回歸社會」的動力
北歐發現,受刑人和外界社會的互動非常重要。而在台灣,每個人從小到大的教育其實都太過於重視他人對自己的看法,許多受刑人在跨入所謂的「社會邊緣」之前,或許沒有太多和他人互動的機會和經驗,導致他們難以精準地表達自己、解讀別人。「舉例來說,幫派之間的逞兇鬥狠經常源於『挑釁』、或是『誤以為別人在挑釁』。」陳惠敏說,「而監獄中的高壓統治,對於改變這個問題並沒有幫助。」
加強外界接觸和社會參與,不但能改善受刑人的社交能力,也可以提昇對於自我存在的肯定,成為「努力變好、努力想重返社會」的動力。但即使是對輕罪犯,我們也很容易忽略自尊對於他們的影響力。舉例來說,台中女監提供受刑人到工業區上班的選擇,但條件是必須戴著手鐐腳銬。「這麼『丟臉』的作法,換做是你我也難以接受,但是受刑人的拒絕反而落了監所的口實,對外表示縱使監所提供了工作機會、這個政策也會因為受刑人的懶惰而失敗。」陳惠敏認為,不給予信任的情況下,很難要求受刑人願意相信社會。
除此之外,目前在獄中沒有被判褫奪公權的受刑人也同樣無法享有投票權,因為服刑地區和戶籍地可能不同,形成監所投票的挑戰。積極推動受刑人投票權的監所關注小組表示:「不過即使區域投票會需要考量受刑人投票的秘密性(避免很容易比對出其投票選擇),為何矯正署不能推動像總統選舉、或是全國性公投這種不分區的投票?正在服刑的人,難道就無權討論他們是否需要核四嗎?如果發生核爆,難道他們不是需要共同承擔的一份子嗎?」陳惠敏從訪調的經驗中發現,有些收容人雖然與世隔絕,但仍很關注社會,「每天讀三份報紙的人都有。畢竟能做的事情不多。」
監獄裡其實沒有「免錢飯」
「去牢裡吃免錢飯」是經常流傳的玩笑話,也容易被誤認為是受刑人再犯的原因。但其實在獄中的飲食與日用品都需要自費。一般來說,加上衛生棉等生理用品,女性受刑人每個月約花費 1,650 元,男性則略少一點。除非有家人接濟,否則即使每天下工場,做著諸如糊紙袋等獄中委託作業的工作,微薄的勞動所得其實難以支應獄中開銷。
剛入監的受刑人還不能下工場,在沒有收入的壓力下,收容人只能跟舍友們以勞動換取日常用品、或接收二手物品、甚至靠幫靠派。這麼做不僅無助於建立受刑人自給自足的能力,甚至可能衍生出受刑人之間不平等的階級關係。
目前政府推動「一監所一特色」政策,各監所致力打造屬於自己的名產,例如南監蛋捲、金門麵線等等。然而即使能夠下工場工作,受刑人也不在勞動基準法保障的範圍,「勞改」的意義遠大於「勞動受薪」。為此,監所關注小組也向矯正署建議為受刑人提供「簡易生存包」,希望受刑人不致於在獄中因為經濟問題而必須加入集團網絡,反而阻斷了出獄後的更生機會。
用「自尊」而非「自厭」,改變無效的高壓治理
全台的矯正機關共有約六萬的收容人,也就是說,有六萬個家庭、六萬乘以很多很多的社會關係相互羅織。「妖魔化」受刑人是台灣社會的習慣,但監所關注小組提出不同的思考角度:
「我們總能很輕易地說別人十惡不赦,卻很少去觀看孕育出惡的土壤。」
在多次的訪調中,監所關注小組發現,多數收容人在成長過程中都處於不被讚美的環境,當少年虞犯進入少年輔育院,老師、所方對待他們的態度,讓他們想當然爾的繼續去做個「壞孩子」,反過來完成社會對他們的反面期待,重複循環影響。
藉由單一的「隔離」思維去處理社會上的惡,監所向社會保證了大眾的「安全」;藉由替獄中之人貼上「都是他們不學好」、「都是他們心理變態」的標籤,大眾定義了自己的「正常」。除了剝奪自由,如果我們能夠打造一個讓受刑人「入獄前」和「入獄後」能夠真正有正向變化的環境,也許社會才能夠減少對於彼此的不信任和集體恐懼。
延伸閱讀:
- 芬蘭監獄的管理之道,台灣可以學習嗎?
- 貧富差距真的會破壞社會穩定,來看李察‧威爾金森在 TED 怎麼說
-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第一個全球性犯罪被害人支持組織VOCI成立〉
- 公民行動影音紀錄資料庫〈真正的高牆,還未倒下?韓國驪州監獄〉
- 獨立評論 @ 天下〈【讀者投書】林俊儒:作為改革倡議的囚犯聲明〉
- PNN 公視新聞議題中心〈開放式監獄的迷思:挪威監獄島巴斯托伊〉
- 苦勞網〈當懲罰失控…應報主義的破產與其他可能〉
按讚,接收更多公益好資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