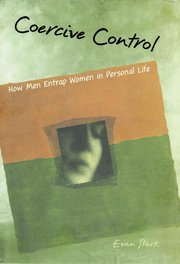受暴女性為何無法脫逃?從社工的專業視角看起
今年三月,阿靜的丈夫政偉因疑心阿靜外遇,對阿靜拳打腳踢,阿靜撥打家暴專線求助。
阿靜的故事
阿靜對我說,她不想再忍耐了,想與政偉離婚,已經開始談協議離婚。但後來,我開始聯絡不到阿靜,原本約定的面談她也沒有前來。
過了一個月,政偉又對阿靜動粗,阿靜向我求助,希望可以尋求庇護住所,我於是為阿靜轉介庇護家園,但從當天中午考慮到下午傍晚,阿靜的態度又轉變了,她決定不入住家園,僅決定暫至娘家住一晚,恢復身心。
我尊重阿靜的決定,但也表達對她的關心,又與阿靜約了要在阿靜親戚家面談。但是,到了約定的那天,阿靜沒有出現、去電不接,阿靜親戚協助我聯繫阿靜,得到「今天家裡有事,不能過來」的答案。返程路上,沒過多久,阿靜突然來電:「希望可以終止服務關係,不需要社工再協助,現在的問題透過夫妻溝通就可以解決,先生也沒有再打,不要浪費社會資源」。
我不解自己做錯什麼,也不知道應怎麼面對阿靜的拒絕,是不是應該要遵循「案主自決」的原則,尊重她現在的決定,先結案、不再打擾她。但同時,又隱約感到阿靜很像典型的受暴婦女圖像,覺得自己好像應該再堅持一下,嘗試瞭解她求助態度的反覆多變。
於是,我開始不密集、比較「不威脅」(不談關係決定)的聯繫阿靜。後來,某一次聯繫時,阿靜對我說,「之前對不起,當時先生在旁邊,所以她只好這樣說」,我們開始約定「秘密暗號」,設定如果講到什麼關鍵字,就代表政偉在旁邊。這個只有我們兩個知道的「秘密暗號」讓我感覺,我們之間好像有點不一樣了。
之後,我到阿靜工作的地方拜訪她,在她繁忙的工作縫隙,斷斷續續的閒聊。這次碰面,加上之前破碎的資訊,漸漸拼湊出一個比較完整的生活世界圖像。
嚴密控管 有如驚弓之鳥
阿靜和政偉結婚多年,有三個小孩。阿靜的工作是基層服務業,工作時有時無。政偉的工作與收入也不固定,一直以來,阿靜家的經濟壓力並不輕。
阿靜與政偉結婚後,政偉常懷疑阿靜與其他男人有曖昧關係,常因此爆發衝突。同時,政偉也對阿靜的生活嚴密控管。阿靜的存摺、提款卡一直以來都被政偉扣住,阿靜一拿到薪水就要全數交給政偉,以讓政偉統一分配,阿靜需要買菜時,政偉才會給阿靜幾百元。因為政偉的善嫉,阿靜為了「避免麻煩」,在決定上工前,會先徵求政偉的同意,甚或邀請政偉陪同應徵,經政偉評估許可才會就業。此外,政偉也會不定期查看阿靜的手機、透過家裡的監視器裝置監看阿靜,甚至偶爾到阿靜工作地點查看,使得阿靜不管在哪裡,都很像一隻「驚弓之鳥」,常常都透露著「不要講太多」、「小聲一點」、很想趕快結束會談的神態,這樣的神態,即使是在阿靜工作的地方,都十分明顯。
雖然如此,阿靜仍心心念念要給孩子一個「完整的家」,希望小孩在有爸爸、有媽媽的家庭中長大成人,於是選擇體諒政偉的善嫉、暴力,而對自己的情緒、感受,總是以「好了,現在先不要說了」來止住快要流出的淚水。
重新理解阿靜:受困於暴力處境
阿靜的故事在家暴防治的工作中雖不陌生,然而,由於台灣目前家暴事件的介入工具以司法取向為主(例如:聲請民事保護令),因此在實務上,社會工作者或網絡工作成員也養成了較重視「看得見」的肢體暴力的習慣,而容易忽略精神暴力、嚴苛管控的受暴處境。
長期研究家暴議題的學者 Evan Stark 分析,雖然有許多工具能讓受暴婦女保護自己,例如庇護所、家暴保護令,但這些作法多僅能保障受害人短期的人身安全。長期來看,除非能看見、並處理受暴婦女在日常生活中經驗的壓迫,否則仍難以協助受暴婦女獨立、獲得自由。同時,因外界與服務體系習慣以暴力事件為指標,而忽略日常生活控管關係的「連續性」與「反覆出現」,使得服務體系傾向假設在暴力「事件」與「事件」之間,受暴婦女有離開關係的可能性;因此,有時服務體系甚會進一步對這些婦女貼上標籤,質疑她們「心理有問題」,否則,她們為什麼不離開?
他進而提出「高壓控管」(coercive control)這一概念來理解受暴婦女,從「男人怎麼將女人陷入(entrap)受暴處境」這一視角出發,討論個別男性作為「性別優勢」群體中的一員,如何利用社會既有的、對男性群體有利的性別意識、以及各種手段(暴力、威脅、孤立、剝奪、剝削、管制、貶抑等),使女性陷入受暴關係、難以逃脫。因此,他認為外界對受暴婦女的想像與疑惑是搞錯對象。應該質問的對象是男人不是女人,該問的問題是:「男人用什麼手段將女性受困於暴力處境,使女人難以離開?」而不是問女人「妳為什麼不離開?」
對應阿靜的故事,「高壓控管」視角準確地解釋了她的困境,政偉的嚴苛控管使阿靜成了驚弓之鳥,不僅難以擺脫傷痕累累的關係,就連對外求助、尋求正式體系的奧援也不容易。
同時,性別結構的推波助瀾也在阿靜的受困中,有著或深或淺的痕跡。父權社會賦予男性伴侶對女性理所當然的佔有欲與貞操監控;阿靜對「有父有母」才是「完整的家」的家庭想像;阿靜堅忍不拔、收斂情緒的自我規訓,是她對「好女人」的想像內涵。這些根深蒂固的既有意識,都在阿靜受困的處境中作用。
政偉對阿靜的孤立策略,也十分成功。由於阿靜對外求助、警政約制告誡、或讓政偉發現阿靜有與社工連繫,都會讓阿靜遭受更嚴重的暴力對待,因此阿靜在危機過後,傾向選擇明快地向警察、社工說明家裡沒有無問題、不需要幫忙,並很小心地與社工連繫,以保全自身安全。
與阿靜談到她拒絕社工服務的那一天,她說,政偉當時要求她把手機開到擴音,她心想,眼下「只能得罪某一方」。聽阿靜這樣說,我越來越明白,她對體系與社工的拒絕,其實是她維護自身安全的策略,是她對政偉「輸誠」的展演:既然沒有要離開,政偉又(因對阿靜行為模式的把握)不怕體系的監控,她只好以拒絕體系,換取短暫的安全,但是,當她選擇這樣做時,也使自己陷入了更被隔離的處境。
這裡說的「隔離」指的是隔絕於體系之外。
阿靜幾年前阿靜就曾通報進案,阿靜曾先後被多位社工服務過(在我之前協助的社工已離職),期間更曾出現過兒子受暴,兒保社工的介入使得阿靜嚴重受暴的狀況(政偉以為是阿靜通報,因此對阿靜嚴重施暴)。或許因為阿靜對體系傾向不說太多的習慣,加上後來養成、對體系的排斥,使得阿靜雖從多年前通報進案,但一直難以被深入瞭解、進入長期服務歷程,而社工也比較傾向在離職時結案,而非轉介其他社工續處,造成阿靜一再進案、由不同社工服務的狀況(當然,社工的流動又是另一個可探討的議題)。
另一方面,政偉卻積極整飾自己的印象。警局的家暴防治官約制後,形容政偉「文質彬彬、很有禮貌」,認為阿靜說詞反覆,講的可能都是「以前受暴的狀況」,是個「很奇怪、有問題的女人」。一來一往之間,阿靜在家暴體系監控中節節敗退,成為「奇怪、難工作的求助者」,反倒是政偉,贏得了警政的信任。
家暴防治體系的侷限
回顧至今的服務歷程,我曾向阿靜抱歉,過去的警政約制不僅沒有幫到她,反而造成了她的麻煩,也向她道歉,過去換了這麼多個社工,使得每次社工都要重新認識她。沒說出口的抱歉是,面對她現在的處境,似乎家暴防治體系並不能有效地協助他。
目前的家暴體系中,多以司法工具使用為主,不僅政府的家暴宣導以此為主要焦點,社區網絡(警政、社政)的合作與協助也多以此為基調。不可否認,保護令、警政體系的約制告誡,確實能協助到部分家庭暴力被害人。然而嚴重的「暴力事件」的並不會構成「受暴處境」,關係中是否存在權力地位的不對等、是否有一方對另一方透過各樣策略脅迫管控,才是親密關係暴力議題的核心。
然而,在目前家暴防治體系的運作下,阿靜的求助卻似乎難以得到有力的回應,甚至因為警政的約制告誡使得阿靜的危機程度升高,接著,又因為政偉的監控與孤立手段,使得阿靜傾向拒絕體系,成為不積極、不合作的「奇怪個案」。
這映證了 Stark 的觀察,在目前家暴防治體系中,由於強調法律工具的介入,家庭暴力被「事件化」,視為彼此無關、獨立的暴力案件;反之,他認為親密關係暴力中,關係脈絡以及權力地位才是更該被關注與處理的重點,嚴密掌控的「總和」對受暴婦女的影響才應是被探究的。針對單一事件的個別處理,不僅難以進入受害者的主觀世界,理解她的日常生活,也很難有效地協助受害者。針對這樣的受暴處境,Stark 認為「命名」是首先應當做的,接著,除了在司法體系中認知到受暴關係對受害者的「累加」效果外,扭轉性別刻板印象、改善社會中的性別不平等現象也需同時並進地努力。
回頭看阿靜的故事,Stark 的分析提供了一個思考方向,從家庭暴力到「高壓控管」,值得實務工作者與網絡細細再思。
延伸閱讀》
艾瑪·華森之外,其他歐美女星敢不敢承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者?
photo credit: @Doug88888 via photopin cc
按讚,接受更多公益深度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