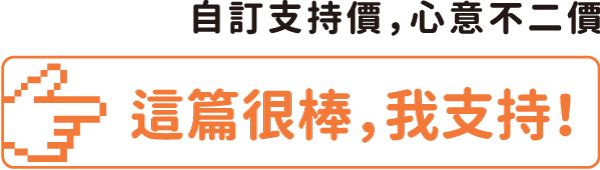現代社會福利制度起源於 17 世紀初的英國伊莉莎白法案,而社會工作專業的發展多數認為是 20 世紀以美國的社會發展模式為基礎。助人工作自這 2 個重要的時期,正式鑲嵌在國家與政府的制度化結構之下。但社會福利歷經了 400 年、社會工作專業發展了 100 年,這樣的制度與專業究竟是助人為多?還是隱藏著篩選社會成員,並排擠弱勢族群為多?
加拿大原住民社會工作的發展,包括 19 世紀末期以白人、基督教會為主導的寄宿學校(Residential Schools),強制將原住民兒童帶離家庭,實施種族同化教育;以及 1960 年代,以社會工作的「救贖」為名義,將那些在西方標準下落入「照顧疏忽、虐待」的原住民兒童,強制安置到白人中產階級家庭。這 2 個社會福利工作的實施,時至今日,經過長期的調查,都被定調為「種族滅絕」(Genocide)。對於那些倖存者(survivor)而言,多數都有跨世代的身心創傷,導致家暴、藥物與酒精濫用、暴力犯罪、貧窮、自我認同的混淆與文化流失等,在短期內再多的社會福利資源都無法翻轉。

但是,加拿大的歷史能給臺灣帶來什麼樣的啟示?
制度性的檢討。
以上 2 個重要的制度性檢討中,有些當初的牧師、社工或政府官員被起訴,尤其是針對曾利用這個制度,進而性侵害、虐待等違反「刑法」的行為。而社會工作社群,並不負責內部倫理審核去處罰相關人員,而是走向討論如何在法定架構與責任下,察覺自己是否順服的扮演制度壓迫的幫兇。
猶如 2013 年在 SK 省發生的悲劇,2 個因為家庭失能而被安置的原住民孩子,在寄養家庭一起帶去公園玩耍時,其中一個患有胎兒酒精中毒症候群(FASD)的孩子,突然對另一個孩子施暴致死。翌年,兒童權利委員會(child advocate)做出調查結案報告:Two Tragedies: Holding systems accountable。裡面當然提到社工員在做出安置決定的時候,犯了那些判斷與評估的錯誤。但報告的重點,卻是放在整個社會局與相關機構,對於評估工具、教育訓練、內部督導、跨機構協調、家庭工作、工作流程與細節的設計,甚至於人力資源的應用和配置等「結構性因素」做出檢討。
社工員的個人疏失幾乎著墨不多。為什麼?因為社工員的所作所為,是被更大的制度推著走,亦如管理學的定律,「制度影響行為」。制度是維繫服務品質的關鍵,決定了社會工作者是否一出門至少都有 60 分的及格水準;而社會工作者的能力和個人特質,最多只會占那 60 分到 100 分的部分,比重無法與制度相比,更何況助人實務沒有所謂的 100 分。
換言之,如果機構雇用的社工出門達不到 60 分,機構要檢討內部的雇用和訓練品質,為什麼養不出及格的工作人員;如果機構普遍找不到 60 分的社工來雇用,專業社群要檢討自己為什麼教育不出及格的社工畢業生。當然,所謂及格、教育、門檻的部分,都需要更多細節討論,並且要重新定義什麼是「助人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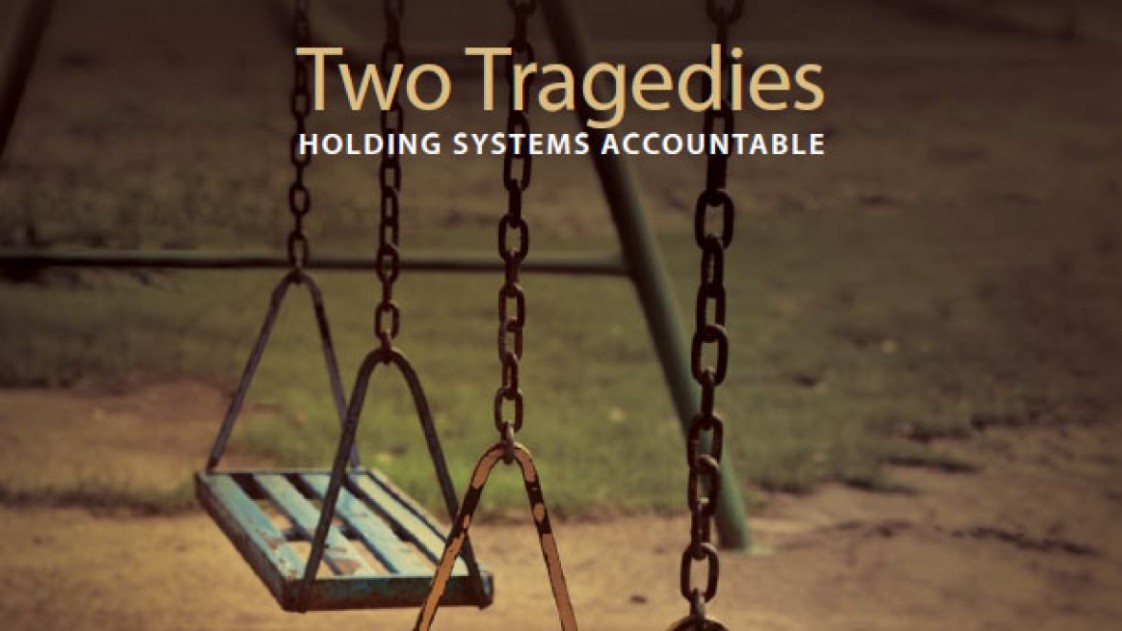
回頭來看,臺灣最近的 2 個事件,(參考「從倫理審議制度,看臺灣社會工作專業社群真正的困境」、「失控摔死11歲男童 育幼院老師遭收押」),我看不到太多對於機構與制度的檢討。
基本上,倫理的審議以符合社會趨勢有其必要,但臺灣社工專協審議新版的倫理立足點錯得離譜。倫理保障的是服務對象,更是實務工作者。但是性侵害或虐待的避免,是助人工作,或者說任何一個守法公民的 ABC。可以規定不可以和服務對象上床,只是如果是兩願合意,社工專業倫理只能夠將其除名作為處罰,刑法一點責任都沒有。可以規定不可以照顧疏失或虐待,只是一旦發生,社工倫理也還是只能將其除名,其他是刑法或兒童福利法的公訴程序。所以,與其去審議倫理,不如同時去檢視現有的社福機構和單位,對於內部控管、訓練、服務流程、人力配置等狀況是否造成照顧人力的高張力。
只是,老話一句。「要是臺灣的社會工作權威社群有這麼積極的作為,那才是會讓我吃驚到掉下巴的新聞了。」
後記
對於育幼院老師的行為對錯,在沒有公平調查的結果前,我沒什麼好說的,該起訴就起訴。但讓我好奇的是機構內部的教育訓練和督導管控在做什麼?為什麼出了這件事之後,沒聽說要停業進行全面調查?又,如果是我做錯事被主管打巴掌,我二話不說會告主管。因為任何人都沒有權力以這種方式實踐他們自以為的正義。
當然,臺灣習慣自以為正義去毆打嫌疑犯或罪犯,也很少看到有人因此被告。其實,這是臺灣法治發展的悲哀,背後代表的是,臺灣社會對於政府、法治和專業沒有信心。
本文經作者授權轉載,原文刊載於此。